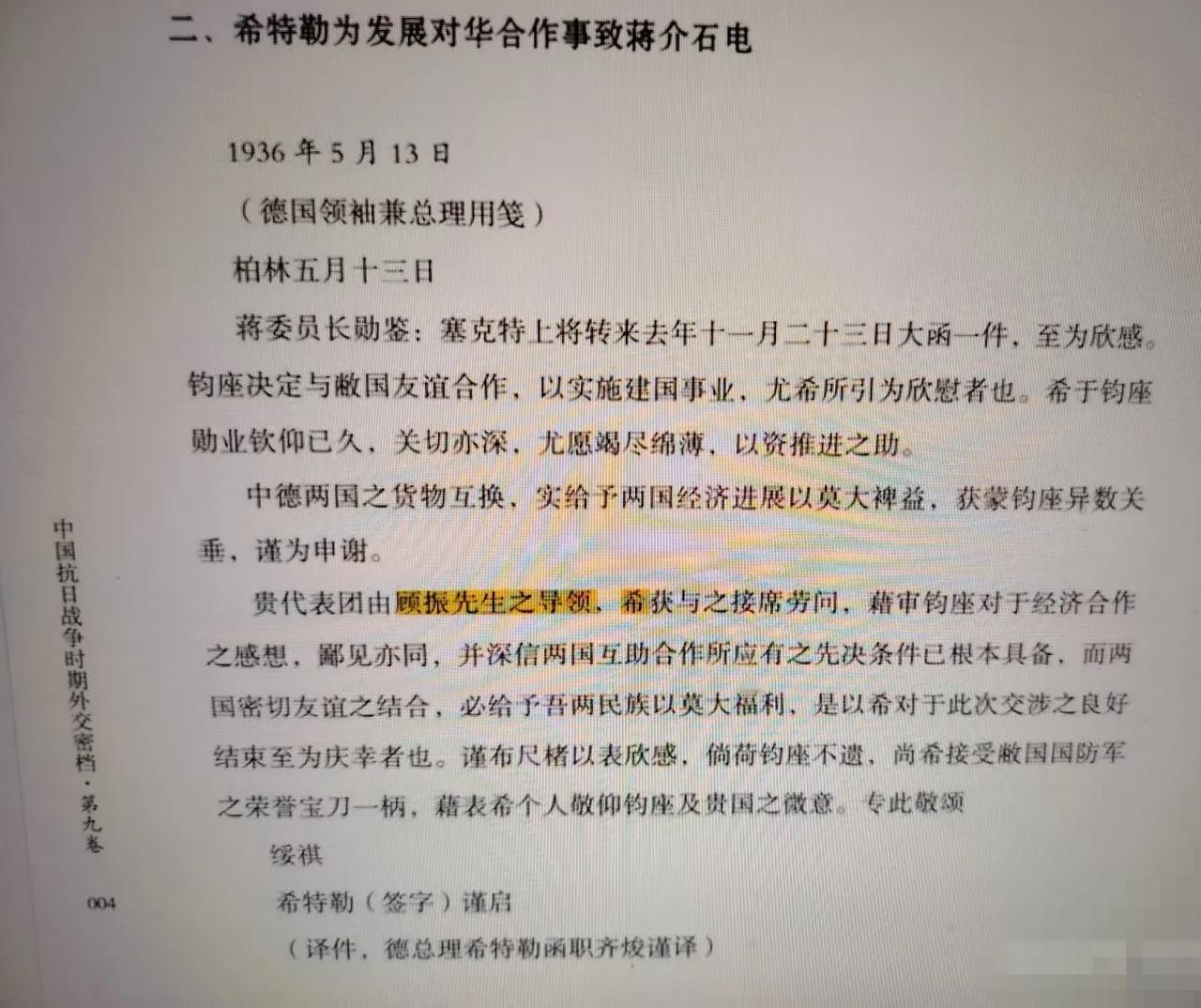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已是第二次邀请了,可是,青年还是没有答应。 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生厉声教,刚满21岁,三次拒绝外交部的邀请。 拒绝背后没有口号,没有姿态,只有明确选择。 第一次邀请,发生在毕业前的9月,外交部干部科派人找到他。 来人态度不卑不亢,说部里需要人,厉声教听完没答应。院里反复劝,劝他放弃理学转向外交。 他说:“我学地理是想研究国土开发,不是去谈判。”干部科记下这句话,没有劝第二句。 第二次邀请,出现在国庆节之后,这次来人换了。 条约委员会一位副主任和干部科领导一道登门。 南大招待所小院里,三人落座。对方坦白说,外交系统缺少精通自然地理,和语言能力兼备的人才。 他低头听完,嘴角抽动一下,说:“可我没这个兴趣。” 三人气氛一度冷场。副主任咳了两声,说:“国家培养你八年,不考虑国家需要?”厉声教看着他,没有回答。 回房后写了封信,递到系里,明明白白写:“暂不考虑入部。” 第三次,外交部动用了刘泽荣。 不属于外派那种能走动的官员,70多岁,翻译条约近40年,早已不露面。 可这一次亲自来了,见面没有寒暄,只有一句:“我看过你写的那篇《中缅边界地貌分布》,你说‘边界并非抽象线,而是实际使用权’,这句话,我记了三天。” 厉声教站着,没说话,刘泽荣往前推了推:“你不进来,我这几十年白干。” 他像听到一声重锤落地。第二天一早,把答复带到系里。 纸上只写五个字:“愿随刘老行。” 这一决定,引起外交学院内部震动,一名非党员、非团员,以理科背景进外交部,在当时绝无先例。 档案上批注:“特例录用,政治考察从简。” 有人说破格用人,有人说是学术赌注,但条约委员会没人反对。 进外交部三个月,刘泽荣交给他一份文书,是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稿。 译稿已被退回两次,原因是“海域边界定义不明”。 厉声教看了三天,写下两万字对照分析。 第四天把一张表交给刘泽荣,上面写明:12海里领海划界与专属经济区,200海里资源开发权利的区别,并加注:“如混用,将在国际诉讼中失先。” 刘泽荣点头。批示上写:“交厉校对,不需返审。” 那一年,中国未被邀请正式参会,只能做外围观察员。 但这份翻译,后被用作外交备忘参考文书。 1973年,一场因某西方国家,误将我方‘专属经济区’译为‘领海’引发的外交交涉,最终通过这份文书理顺。 周总理得知后,批示六字:“此子可重用。” 而在这之前,厉声教还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旧外交文件,厉麟似的文稿、诗稿、谈判记录,铺了一地。 有人来问:“你这是在做研究?”他头也不抬:“是对自己的提醒。” 他没有走典型路线,连培训期都被跳过,直接调入条约委员会研究组。 第一次参与正式工作,是中缅边界初步勘界会议。 会上,他一句话未说,会议结束却递上两页资料,用英文标注出自然分界线,与村落生活区重叠处。 缅方代表看后,将原提议作出修改。 没有任何表扬,回程火车上,刘泽荣只说了一句:“多想两步。”他点头。 那晚在车厢里写下会议纪要,未交由翻译,自己誊抄三遍。 再后来,去多伦多任副总领事,调巴巴多斯做代理大使,协助边界谈判,参与海洋法草案起草。 每一步都不显山露水,但都留下痕迹。 几十年后,有人整理中国外交文件时发现,数十起边界与海洋争议谈判中,起草稿中署名最多的正是他。 他不说豪言,做事精准,别人写报告三页,他写一页附图。 别人谈论策略,他计算潮汐表与地形线。 有人问他为何不留校当教授。他回:“纸上得来终觉浅。” 有人问他为何不入党。他回:“先把事做好。” 直到晚年,有人提起当年三拒外交部之事,他只说:“多走两步,多看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