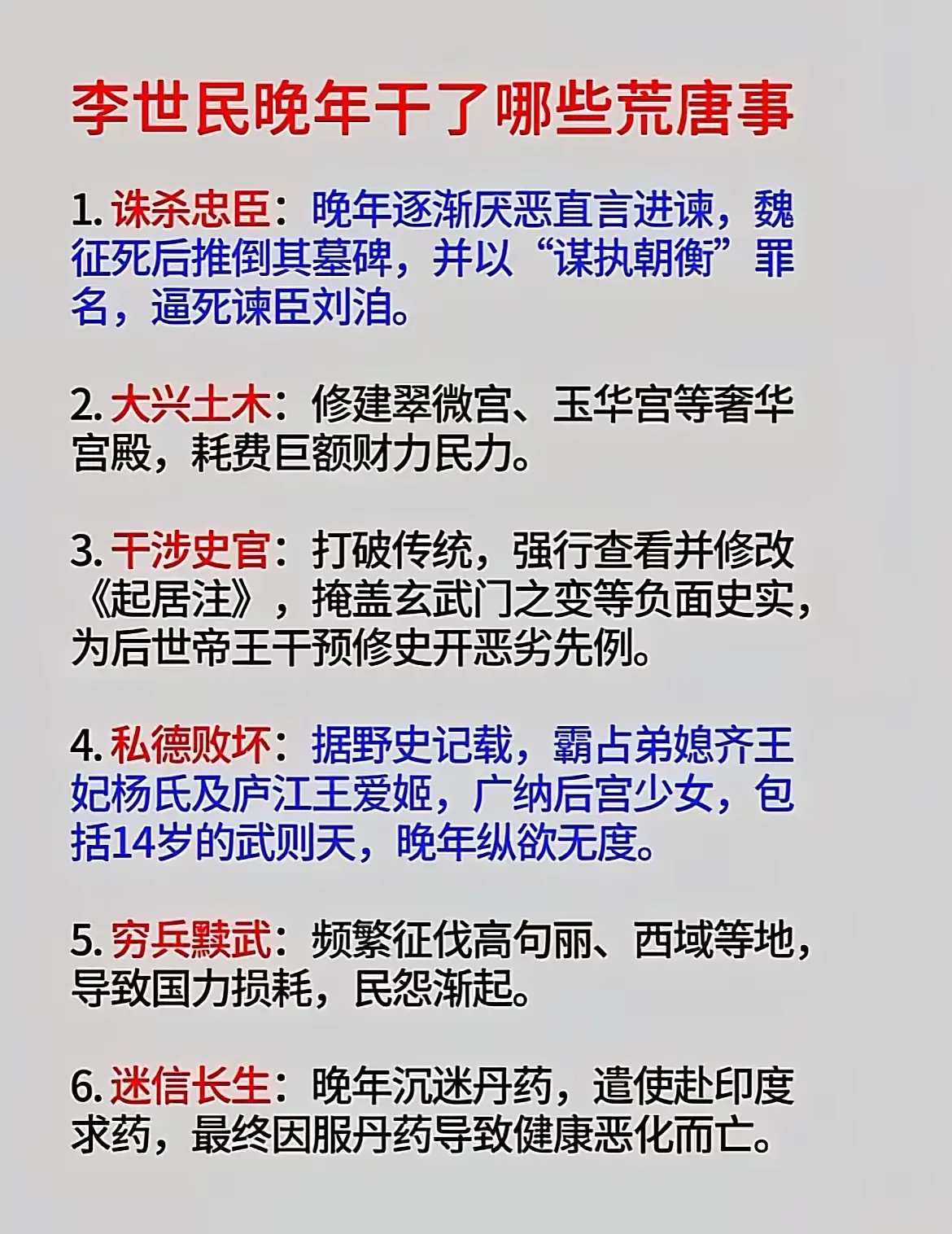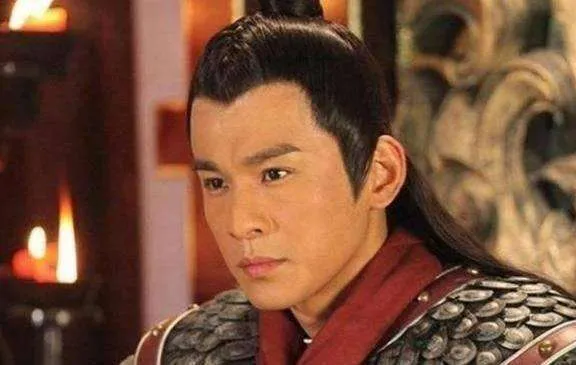626年,27岁的李世民搂着寡妇,参加玄武门庆功宴。长孙无忌见状,一手握拳捶在桌案上:“我妹妹怎么办!“李世民警了他一眼,手警一紧,把寡妇按在了自己的两腿间,稳稳当当落座。 玄武门血迹未干,长安城却已张灯结彩。宴会上,李世民搂着杨氏入场,群臣屏息。 殿下群臣推杯换盏的喧嚣瞬间静止,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女子身上。长孙无忌坐在首席,紧握的拳头青筋暴起,眼神如刀,却一言不发。 要解开这场宴会的悬念,还得回到数日前那个血腥的清晨。626年7月2日,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晨雾未散,李世民身披铠甲,立于临湖殿前。马蹄声由远及近,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并肩而来,毫无防备。 “皇兄,皇弟,留步!”李世民的声音低沉却冷冽。两人骤然止步,察觉异样,却已晚了。玄武门守将常何——早已被李世民收买——一声令下,大门轰然关闭。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亲信从暗处杀出,李世民亲手搭弓,一箭射穿李建成的喉咙。几乎同时,尉迟敬德的箭矢洞穿李元吉的胸膛。 战斗不过片刻,玄武门血流成河。湖面倒映着晨光,泛舟海池的李渊被尉迟敬德“护送”回宫,面对儿子的武力逼宫,这位开国皇帝只能无奈下诏,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改元贞观。 那一夜,李世民未眠。他站在玄武门城楼,俯瞰长安灯火,低声自语:“社稷为重,兄弟何惜?”但烛光下,他的眼神却透着一丝复杂——是胜利的喜悦,还是弑亲的隐痛? 庆功宴是李世民向天下宣示权威的舞台。太极殿内,功臣们齐聚,酒香弥漫,歌姬起舞。然而,杨氏的出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杨氏并非普通女子。她出身隋朝名门,是杨素的孙女,早在少年时便与李世民相识,彼此情愫暗生。玄武门之变后,李元吉身死,杨氏孤苦无依,李世民以“抚养其女”为名将其接入宫中,实则纳入后宫。这一举动,既是旧情复燃,也是政治考量——杨氏的家族势力能助新帝稳固朝堂。 但群臣眼中,这却是新帝的“失德”之举。根据《唐律疏议》,私养别宅妇或与逆贼家属过从甚密,皆为不法。更何况,杨氏的身份敏感,她的出现仿佛在提醒众人:玄武门的血腥尚未远去。 长孙无忌的沉默最为刺眼。作为长孙皇后的兄长,他既是李世民的连襟,也是玄武门之变的主谋之一。他深知妹妹在后宫的地位岌岌可危,却不敢直言——功高盖主的阴影,让他只能隐忍。 就在气氛僵持之时,一道清朗的声音打破沉默:“陛下,庐江王之事,可对乎?” 开口的是王珪,原为李建成旧部,如今被李世民重用。他未直言杨氏,而是以李瑗为例——庐江王李瑗追随李建成,玄武门之变后谋反被诛,其妻被李世民带到宴会,引发非议。王珪的话绵里藏针:陛下若知庐江王杀人夺妻之错,为何还留杨氏在侧? 李世民一愣,笑容渐收。他扫视殿内,目光在长孙无忌的怒容与王珪的坚毅间游移。片刻后,他缓缓点头:“卿言甚是。知恶不去,非帝王之道。” 数日后,李世民下令将庐江王之妻送回族中,杨氏则以“抚养庶女”的名义留在后宫,正式册封为妃。此举既安抚了群臣,也保全了杨氏的尊严。长孙无忌的脸色终于缓和,但宴会上的那一幕,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隐痛。 李世民并非不爱女色。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病逝,他一度欲立杨氏为后,却被魏征以“辰嬴之例”劝阻。魏征直言:立弟媳为后,将重提玄武门旧事,动摇帝王威信。李世民听罢,沉思良久,最终作罢。 正是这种虚心纳谏,让李世民从玄武门的血腥中走出,迈向盛世。他重用魏征、王珪等直臣,推行均田制、轻徭薄赋,平定突厥,尊西域诸国为“天可汗”。贞观年间,户口从200万增至300万,国库充盈,社会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太极殿的烛光渐灭,宴会散场。李世民独坐殿中,手中酒杯已空。他望向殿外夜色,喃喃道:“帝王之路,果真孤绝。” 贞观之治的辉煌,离不开李世民的雄才大略,更离不开群臣的直言相谏。那场宴会上的风波,不过是盛世前的一抹阴影,却也照见了一代明君的成长。从玄武门到贞观元年,李世民用鲜血换来的皇位,最终以仁政泽被天下。 他的纳谏文化,不仅稳定了唐初政局,还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典范——《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年间,谏官上书200余次,李世民多有采纳。这种君臣相得的格局,正是大唐盛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