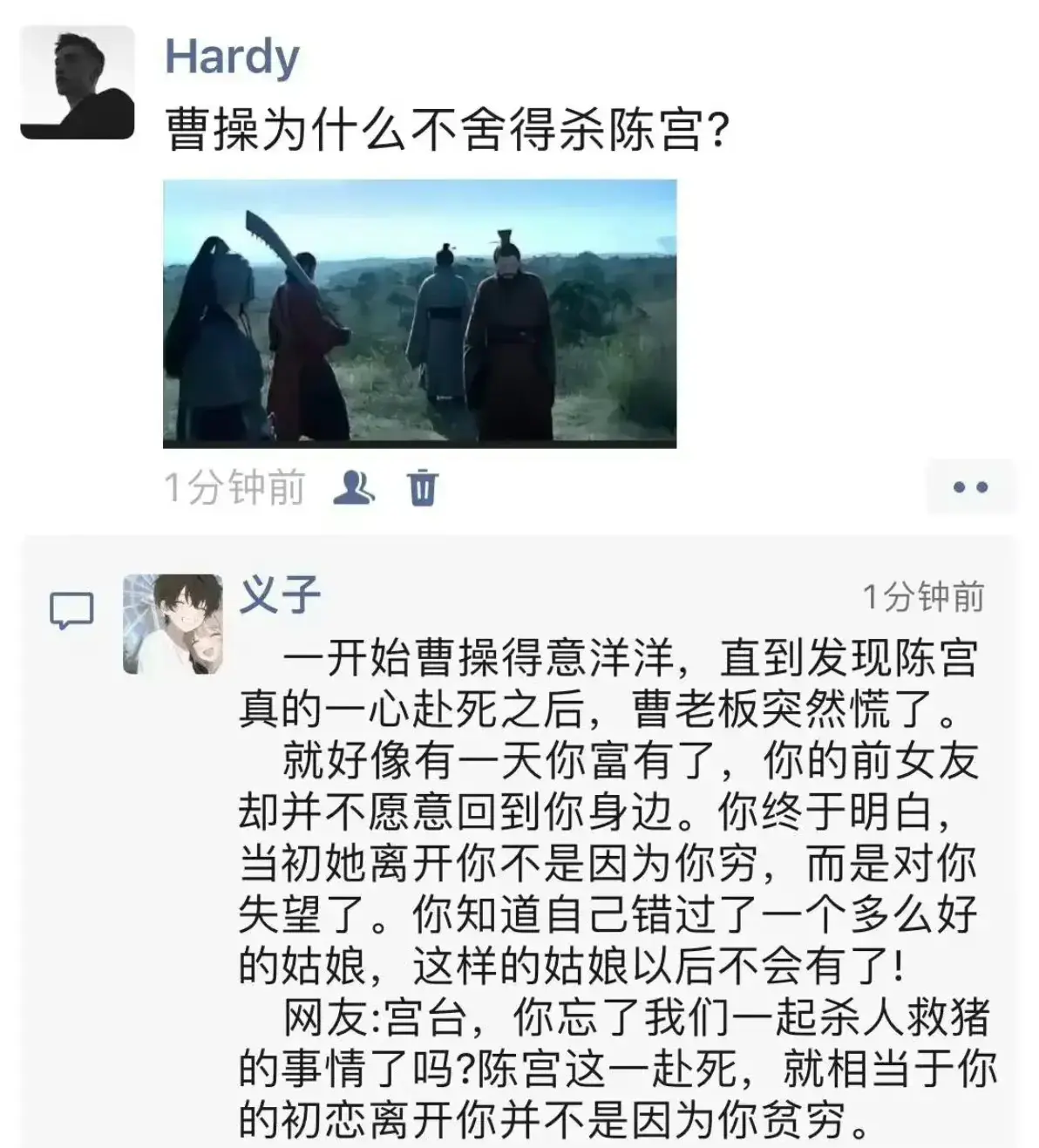1949年深冬,飞机遇寒流,超载需减重。
1949年凛冬,成都凤凰山机场,寒风呼啸,螺旋桨引擎的巨响撕裂着冰冷的空气。机场跑道上的积雪被狂风卷起,足有两米多高。一架美制DC-3运输机,正经历着生死攸关的时刻,它严重超载了。机舱内,弥漫着陈旧雪茄的辛辣气味,58岁的阎锡山裹着厚厚的貂皮大衣,闭目养神,仿佛置身于温暖舒适的家中,盘算着未来在台湾的悠闲生活。 他统治山西三十年,是名副其实的“一方诸侯”。突如其来的剧烈颠簸打破了这片宁静。空乘人员惊慌失措地大喊:“寒流!机翼结冰!必须减重!”
陈立夫,蒋介石的亲信,猛地掀开身上的羊毛毯,暴怒地用皮鞋踹向货舱门,怒吼道:“老阎!你那些箱子,必须扔掉一半!” 货舱内堆满了四十个沉甸甸的柏木箱,每个都重达三百斤,里面装满了阎锡山从山西带出来的金条。 阎锡山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厉声说道:“这是山西百姓的心血!” 他的随从们也立刻挺直了腰杆,像一尊尊僵硬的泥塑佛像。陈立夫冷笑一声,掐灭了手中的香烟:“您倒是替百姓着想,可这飞机可装不下这些‘心血’!”
驾驶舱内传来机长的惊恐喊叫:“最多十分钟!” 机舱温度骤降至零下,乘客们呼出的白雾中,夹杂着绝望的哭泣。 陈立夫掏出手枪,狠狠地拍在货舱板上:“要么扔掉金条,要么抽签决定谁跳下去!” 阎锡山剧烈咳嗽,指着黄花梨木座椅说:“立夫兄,你在苏联中山大学求学时,可曾了解山西票号的汇兑?”他颤抖着解开大衣,露出内袋里一块发霉的怀表,“这些黄金……是晋商百年信誉的象征……”
陈立夫怒斥道:“信誉能当机翼用吗?” 他眼角余光瞥见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胖子正偷偷瞄着舱门,于是他一脚踹翻了三个木箱,金条散落一地,在引擎的热浪中闪耀着诡异的光芒。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机舱。阎锡山捡起一块金条,擦拭着,老泪纵横:“1936年绥远抗战,我用这些金条买了二十万发子弹……” 他身后的随从们压抑着哭泣,有人正将全家福照片塞进行李箱。
刺耳的警报再次响起,陈立夫扯掉领带,露出军统特务的凶狠:“最后一次警告!” 阎锡山拍案而起,死死抓住货舱门:“开枪吧!当年我在娘子关与日寇拼刺刀时,你还给戴笠端茶呢!” 这时,一个随从冲上前,拿出一个雕龙画凤的箱子:“老爷!这是给蒋委员长的拜礼!” 箱盖上赫然写着“民国廿五年航空救国基金”。 陈立夫的枪口颤抖了,他想起了上周宋美龄查空军账本的事。
阎锡山冷笑:“立夫兄,这箱金条的利息,够买你陈家在吴江的祖产了吧?”会计拿出账册,上面清楚地记载着航空委员会的借款记录。 陈立夫脸色铁青,这些账目牵涉到军统北平站的秘密资金。 三个山西籍随从主动站出来,他们被扔进货舱时,还在念叨着阎锡山给他们的军饷。阎锡山喃喃自语:“当年阎百川在五台山当和尚时,可曾想过有今日?”
飞机终于冲破寒流,陈立夫瘫坐在融化的冰水中,发现阎锡山正在清点剩下的金条,他脊背发凉,山西王始终为自己留着后路。 后来的记录显示,这批黄金被洗白,成为蒋氏父子“反攻大陆”的资金。 在菁山草庐,阎锡山常常对着账册发呆,那些用黄金换来的物资,远不及家乡老陈醋的香味。 1960年雨夜,弥留之际的他大笑:“告诉老蒋,那箱航空救国基金……其实是晋祠的古董……” 他床底的黄金,最终被台北的黑帮瓜分,如同他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策,看似精妙,实则自毁长城。 他临终前还在修改回忆录,上面写着:“黄金重还是人心重?” 这个困扰他一生的问题,或许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中能找到答案。如今,凤凰山机场早已废弃,但老兵们说,每逢阴雨夜,还能听到金条撞击的声音——那不仅仅是黄金,更是晋商文化的信用体系。 当“山西王”选择用黄金而非道义续命时,便注定要承受这孤独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