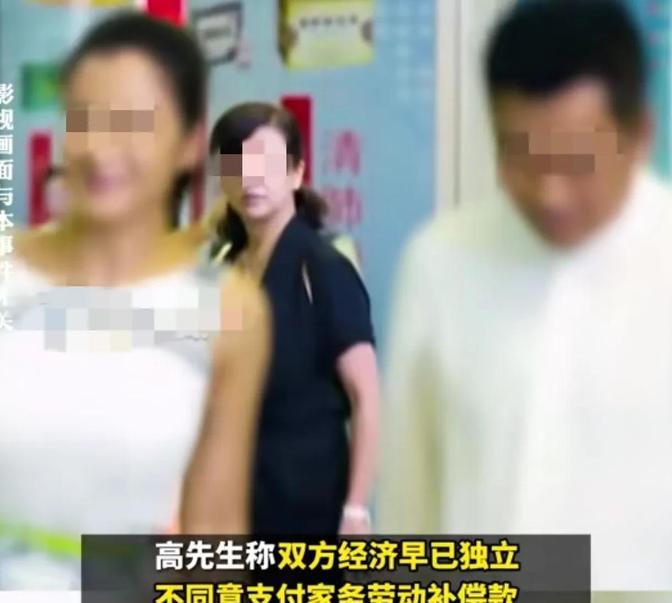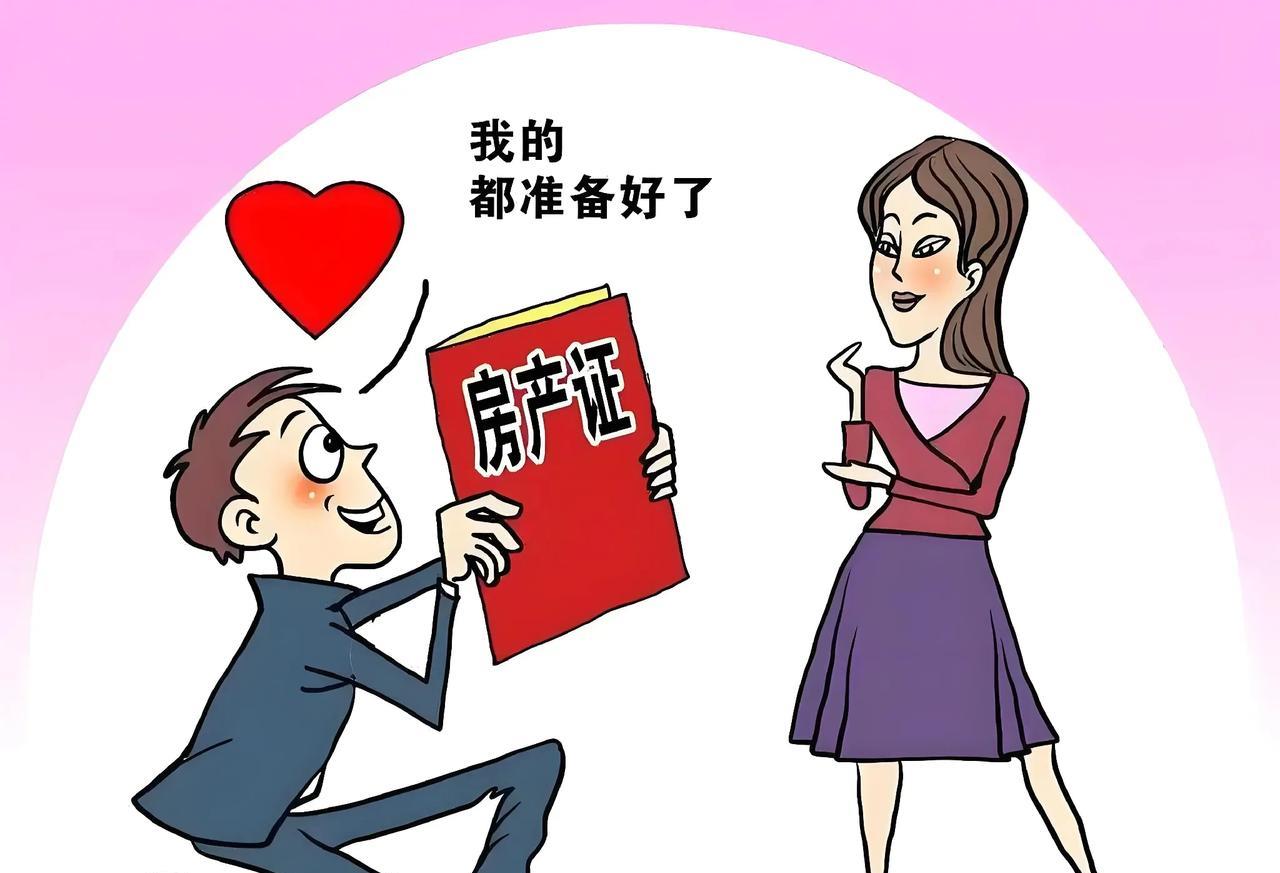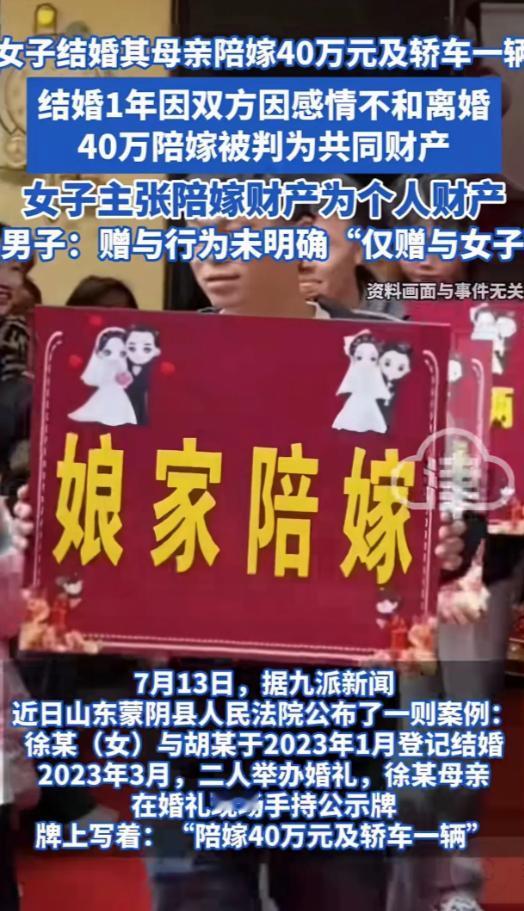上海,一男子发现妻子迷上了某平台男主播,在一年多里,妻子不仅疯狂打赏90多万,还私下微信转账10多万给男主播,聊天内容暧 昧,甚至线下见面见家长。男子无法接受,选择离婚,并一纸诉状将男主播告上法庭,要求返还55万夫妻共同财产。庭审中,男主播辩解说打赏是给平台的消费,不是直接赠与他。但法院看穿了本质,认定巨额打赏远超娱乐消费,加上暧 昧聊天和转账等,就是为了维系特殊关系,这就是变相赠与,依法作出裁判。 2025年7月14日,据澎湃新闻报道,黄先生与李女士于2014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双方从未约定过夫妻财产分别所有。 黄先生无意中发现,在2021年9月至 2023年2月,李女士频繁在刘某的直播间进行打赏、刷礼物,累计金额高达90万余元人民币。刘某在直播中塑造了“勤奋、阳光、腼腆、忠厚”的人设。 李女士还与男主播刘某互加了微信好友,聊天频率高、时间长,内容暧 昧、亲 密,明显超出普通朋友界限。 李女士还通过微信陆续向刘某转账共计10万余元。期间,刘某也曾向李女士转账共计1.6万余元。 2023年2月,两人曾在线下见面,李女士还向刘某父母赠送了礼物。此后,刘某开始回避李女士。 黄先生发现李女士的上述行为后,与李女士离婚。 离婚后,黄先生认为李女士的转账行无效,而男主播刘某应当返还相应财产,遂一纸诉状将刘某告上法庭,请求法院确认李女士对刘某的赠与行为无效,要求刘某返还李女士通过微信向其转账的10万余元以及李女士打赏款90万余元的50%,合计55万余元。 庭审中,黄先生提出如下理由: (1)打赏和转账的钱是黄先生与李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 (2)李女士未经黄先生同意,擅自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侵害了黄先生的合法权益。 (3)李女士与刘某之间存在不 正 当 亲密关系,其赠与行为违背公序良俗。 (4)黄先生称李女士患有较严重的抑郁症并曾住院,刘某利用了其异常精神状况进行诱导。 男主播刘某提出如下答辩: (1)李女士在平台的打赏,是其与平台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并非与刘某本人直接形成的法律关系,也不构成赠与。 (2)刘某辩称自己签约了某传媒公司,根据协议,主播最终获得的打赏收益约为打赏金额的40%左右,且主播需自行承担税费。 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1、李女士向刘某的“打赏”和“微信转账”行为是“娱乐消费”还是“特殊赠与”? 《民法典》第657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男主播刘某虽然辩解其与李女士是打赏服务合同关系,但法院穿透了表面的“服务合同”形式,关注行为背后的法律关系。 李女士对刘某 90余万的打赏,远非普通娱乐消费水平,具有明显的“挥霍”性质。 李女士除了打赏之外,还与刘某有高频、长时间、内容暧 昧的微信私聊,远超主播和粉丝的正常互动界限,还含有“520”等特殊含义的转账,线下见面及见家长行为,共同勾勒出一个超越普通社交边界、具有情感依赖甚至婚外感情色彩的亲密关系。 法院认为,李女士为了维系和发展这种关系,而非单纯购买直播表演服务,金钱成为维系特殊情感的纽带。 因此,法院认定,在这种特定背景下,平台服务合同只是赠与行为发生的一个“渠道”或“工具”,不能改变财产转移的赠与本质。 2、这个赠与行为有效吗?为何无效? 《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涉案款项产生于黄先生与李女士的婚姻存续期间,且双方无分别财产制的约定,是夫妻俩共有的财产,李女士处分原则上需要得到配偶黄先生的同意或追认。 李女士在黄先生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巨额共同财产赠与刘某,侵害了黄先生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擅自处分大额共同财产,原则上无效。 关键是,李女士与刘某的关系违背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破坏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以巨额财产赠与来维系这种婚外亲 密关系,本身就具有道德上的可非难性。 因此,李女士赠与刘某财产侵害了夫妻共同财产且有违公序良俗,依法应认定无效。 3、钱怎么退?退多少才公平合理? 《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 既然李女士的赠与无效,刘某因无效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 但打赏金额并非全部进入刘某口袋,平台要抽成服务费,公会可能分成,刘某还需缴税。要求刘某返还他从未实际获得的平台分成部分,显失公平,也超出了“不当得利”的范围。 微信转账中5.9万被证明是李女士委托刘某用于平台充值,性质已转化为消费,不是给刘某的赠与,故无需刘某返还。刘某也曾向李女士转回1.6万余元。 最终,法院判刘某向黄先生返还30.5万元。 对此,大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