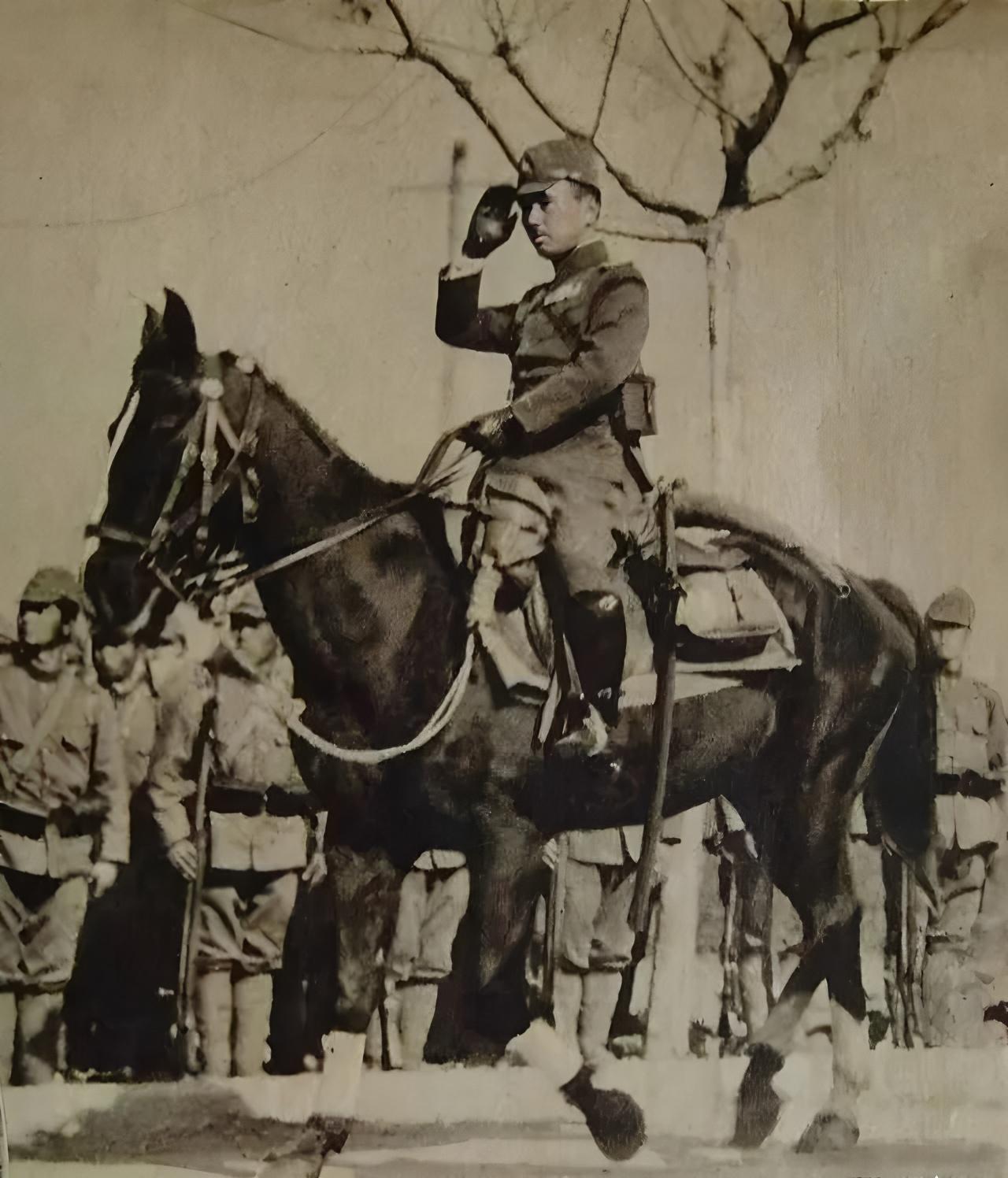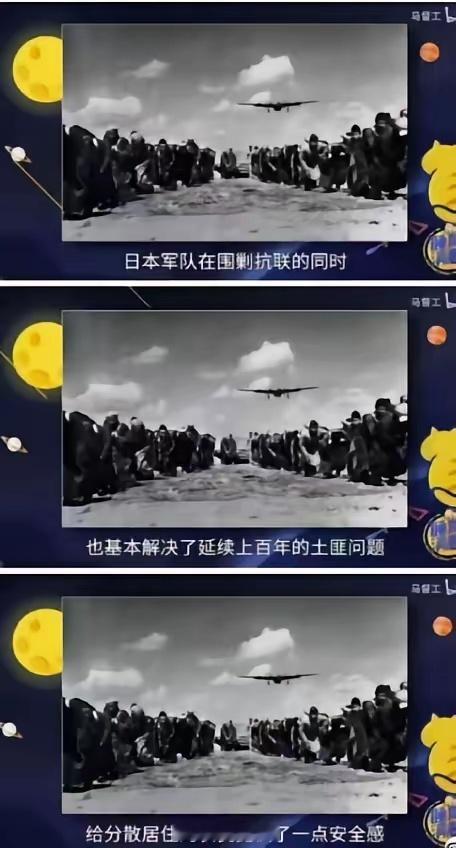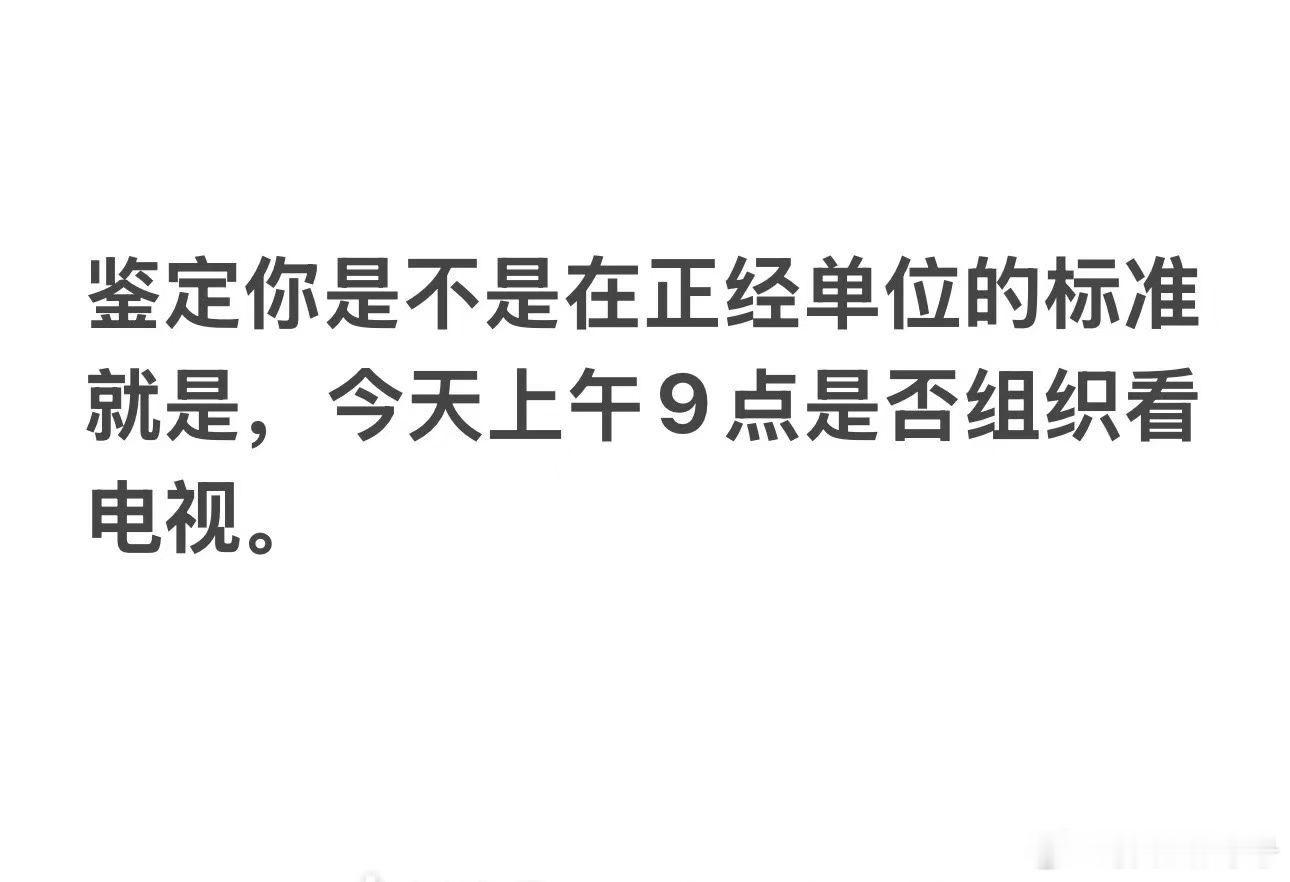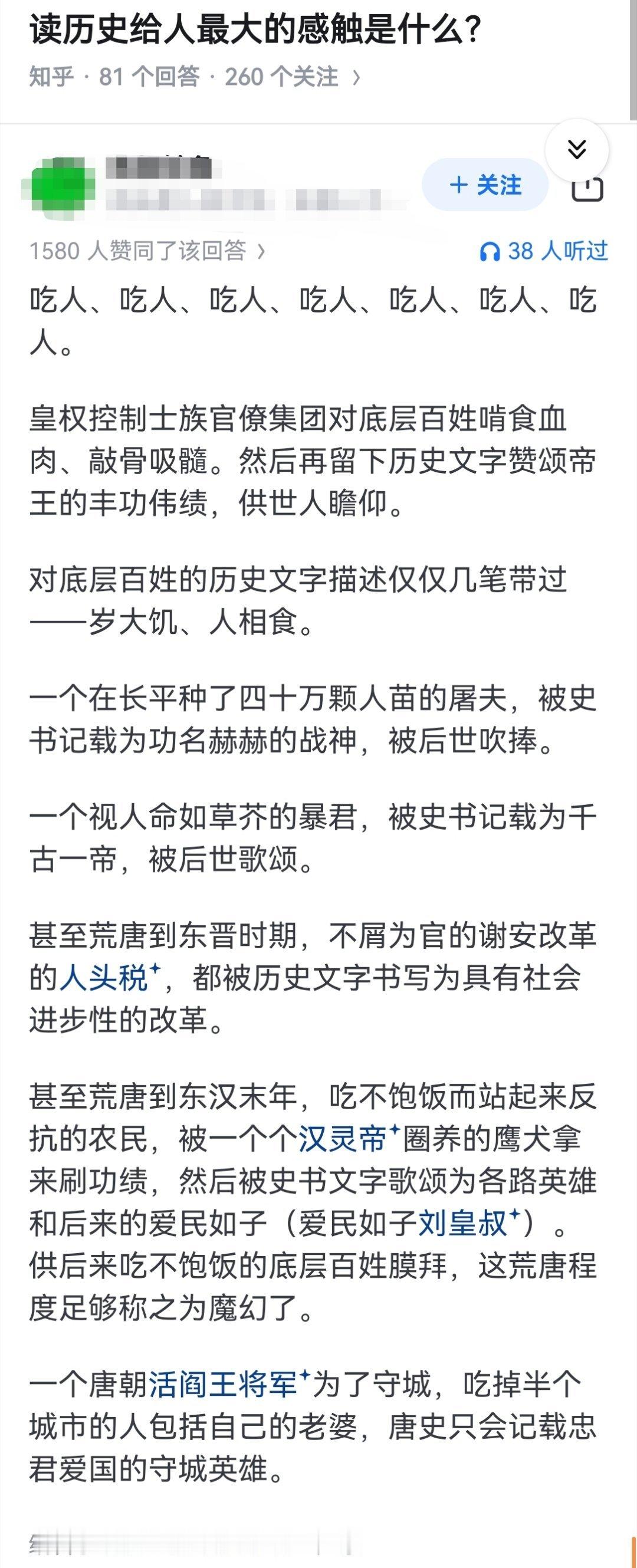1703年,雍亲王正独自喝酒,身旁服侍的侍女,突然走上前低声地说:“王爷,奴婢陪您喝吧!”为了展示酒量,小宫女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1703年的一晚,雍亲王胤禛独自坐在书房外的长廊边饮酒,四下寂静无声,只余酒壶中清液斟入杯盏时的滴落声。 他向来不喜喧哗,府中下人都知王爷饮酒时不可打扰,可那一夜,却有一名侍女突然破例闯入。 那名侍女站在不远处并未行礼,也未等吩咐,只是抬头看了一眼雍亲王,然后慢慢走上前,拿起空盏自行倒满,抬手一饮而尽。 雍亲王微微皱眉,却没有立刻呵斥,他只是放下酒盏,注视着眼前这个身份低微却举止异常的女子,侍女姓耿,是内务府下辖户籍中籍籍无名的一户人家之女。 她年纪不大,入王府后因身形结实被派往园林打杂,负责除草、挑水、扫地等粗重事务,那处偏院日晒雨淋,来往仆役亦无好脸色,耿氏每日奔波劳作,却从未言怨。 她之所以敢冒犯规矩,当着亲王之面擅自饮酒,并非一时冲动,她观察雍亲王已有数月,发现这位主子每日事务繁忙,夜晚常独坐不语,时而低声吟诵,时而长叹无言。 她看得出,王爷虽位居高位,却缺少真正愿意与他同处的人,耿氏明白,若能趁隙靠近,即使失败,也不过被贬出府中;若成功,便是人生转机。 雍亲王对耿氏并无先前印象,见她行为突兀,却又不显张狂,便未当场发作,他反倒产生兴趣,问她缘由。 耿氏没有回避,说自己每日路过花园,见王爷对月独酌,生出几分怜意,她自知身份低微,不敢奢望旁宠,只愿借此替主子解忧片刻。 这番话非媚语不带期许,反令雍亲王动容,其后几日,耿氏被安排调往主院花房,借调之名实则是王爷的默许,两人便自此熟识。 她不多言,常常只是陪着他一边斟酒一边静坐,偶尔提及诗书,但从不触及朝政,雍亲王发现她不同于那些妾室,她不试图探听心思,也不急于讨好,而是静静陪伴,恰如其分。 这段关系起初无名无分,却成为雍亲王心头难得的安慰,数月后,耿氏被正式纳入内院,晋为格格,迁入偏殿居住。 王府内风言风语不绝,然雍亲王并未理会,耿氏亦始终守分寸,从不借宠行事,耿氏进主院前,每日劳作之余,常思自己若无改变,终将老死角落。 她并无奢求地位,只是希望能有一处稳定之所,不再飘摇,她早已明白美貌不足以换来尊重,聪慧也不能保全安稳,唯有谨慎前行,方能长久。 雍亲王身为康熙帝之子,虽为皇四子,实则在诸皇子中并不显眼,他既无母族撑腰,也无兵权在握,为博皇帝信任,凡事亲力亲为,宫务细节无一不察,行事稳重,不露锋芒。 他不如八阿哥那般张扬,也不似太子位高权重,胤禛自知前途艰难,故常深夜独饮,自抚心境,耿氏的出现对他而言是意料之外的平衡。 她既不争宠,也不引事,两人之间的相处不带名分之外的负担,这种清淡的陪伴,让他生出依赖。 数年后,耿氏诞下一子,名为弘昼。那时雍亲王府中已有数位皇子,耿氏没有大张旗鼓,而是默默将儿子交由乳母养育,自身照常行事。 她明白,皇子众多,母凭子贵之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倒是锋芒毕露最易受妒,她亲自教导弘昼,强调礼法与兄弟之谊。 弘昼性格虽倔强,却在母亲的训导下,从未与兄长弘历生出嫌隙,耿氏早早识得弘历资质出众,便常教弘昼以兄长为榜样,言行不可逾矩。 她知道将来皇位不可能落到弘昼手中,与其争位,不如守稳,1722年,康熙帝驾崩,雍亲王胤禛登基为帝,是为雍正。 耿氏未因旧情而要求册封,反而主动退居内廷,不扰朝政,雍正帝念旧情,将其册为妃,赐宫殿安置,弘昼则被封为亲王,另立府邸,自此自成一系。 雍正帝为人严厉,对朝臣狠厉,对后宫也极少流露情感,耿氏是少数能得其恩宠者,她自知份量,从不干预政务,也不与后宫诸妃交锋,宫中对她皆敬而远之。 她反倒因此在后宫中活得最安稳,既不受排挤,也不遭妒忌,弘昼成年后,性格渐显张扬,但在关键时刻从未失礼。 雍正帝对其既赏亦限,不予政权,却不剥爵位,耿氏多次暗中劝诫弘昼,务必谨慎,不可贪权,她明白帝王心中最怕的便是兄弟之争。 她能活得安稳,不是因为恩宠,而是因为从不越雷池一步,乾隆登基后,弘昼虽失权力,却保爵封地无虞。 耿氏年事已高,居于偏殿,不出宫门,她不干政,不干事,甚至不干涉儿子的府务,只安然守住自己的世界。 她见证了三代皇帝,从妾室到妃,从宫女到王母,却始终未曾逾越一步,她的名字鲜有人提及,但所有后宫记事中都记录着她的清醒与低调。 最终,她寿终正寝,送殡之日,乾隆帝亲遣内务府总管主持,弘昼亲赴灵前致哀,皇室档案只留一句:“耿妃,性恬淡,行谨慎,事无违纪,卒于安养。”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清史稿·后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