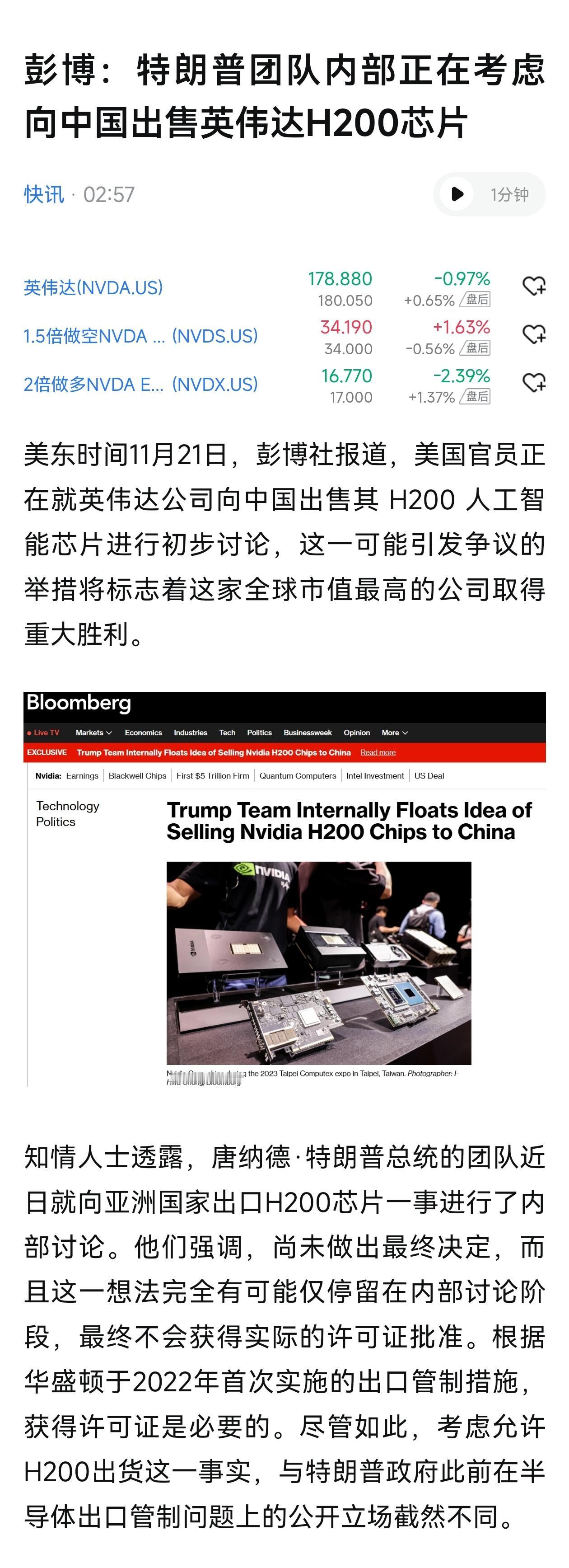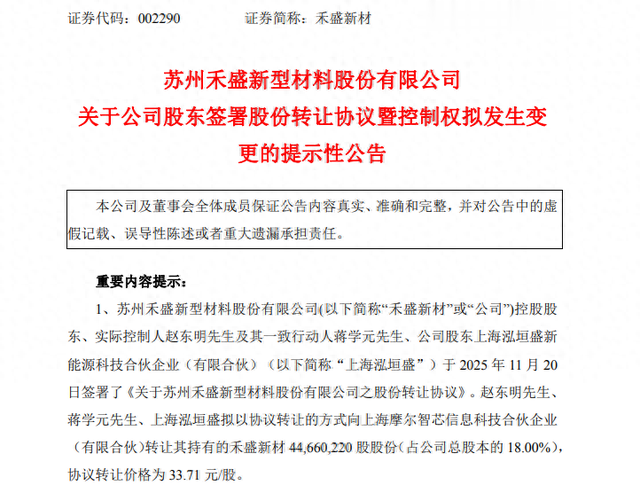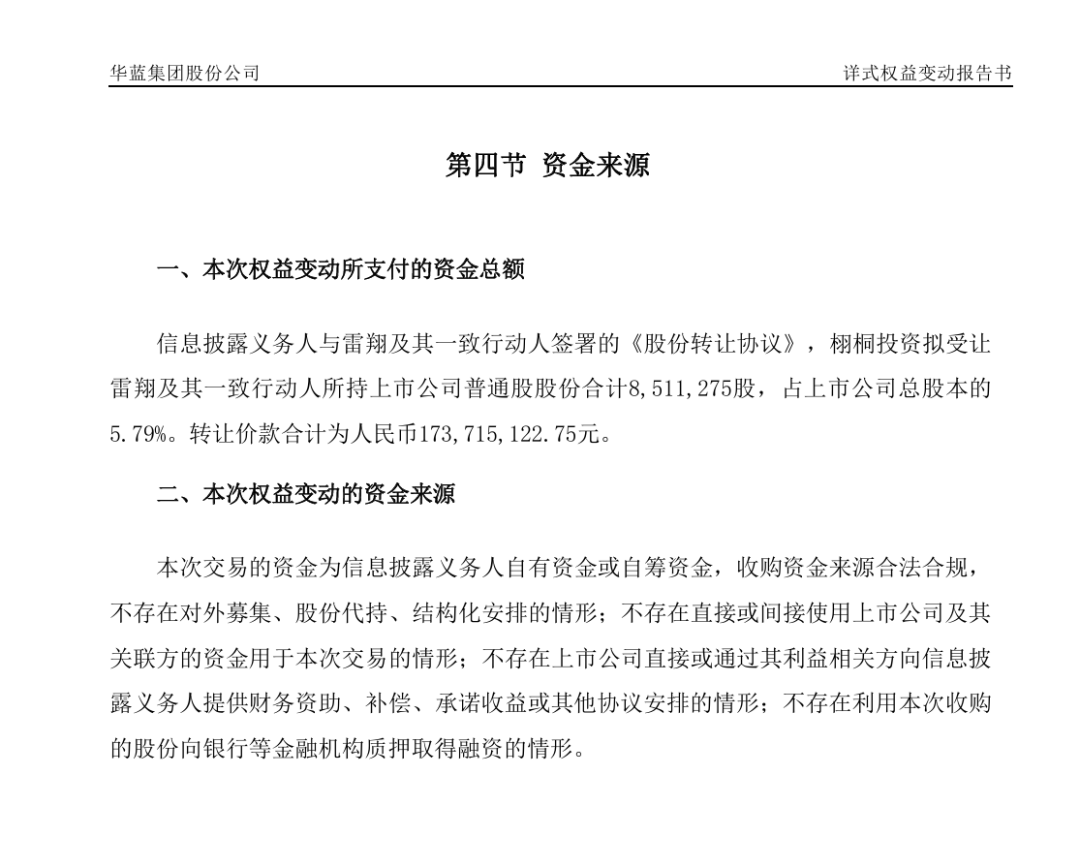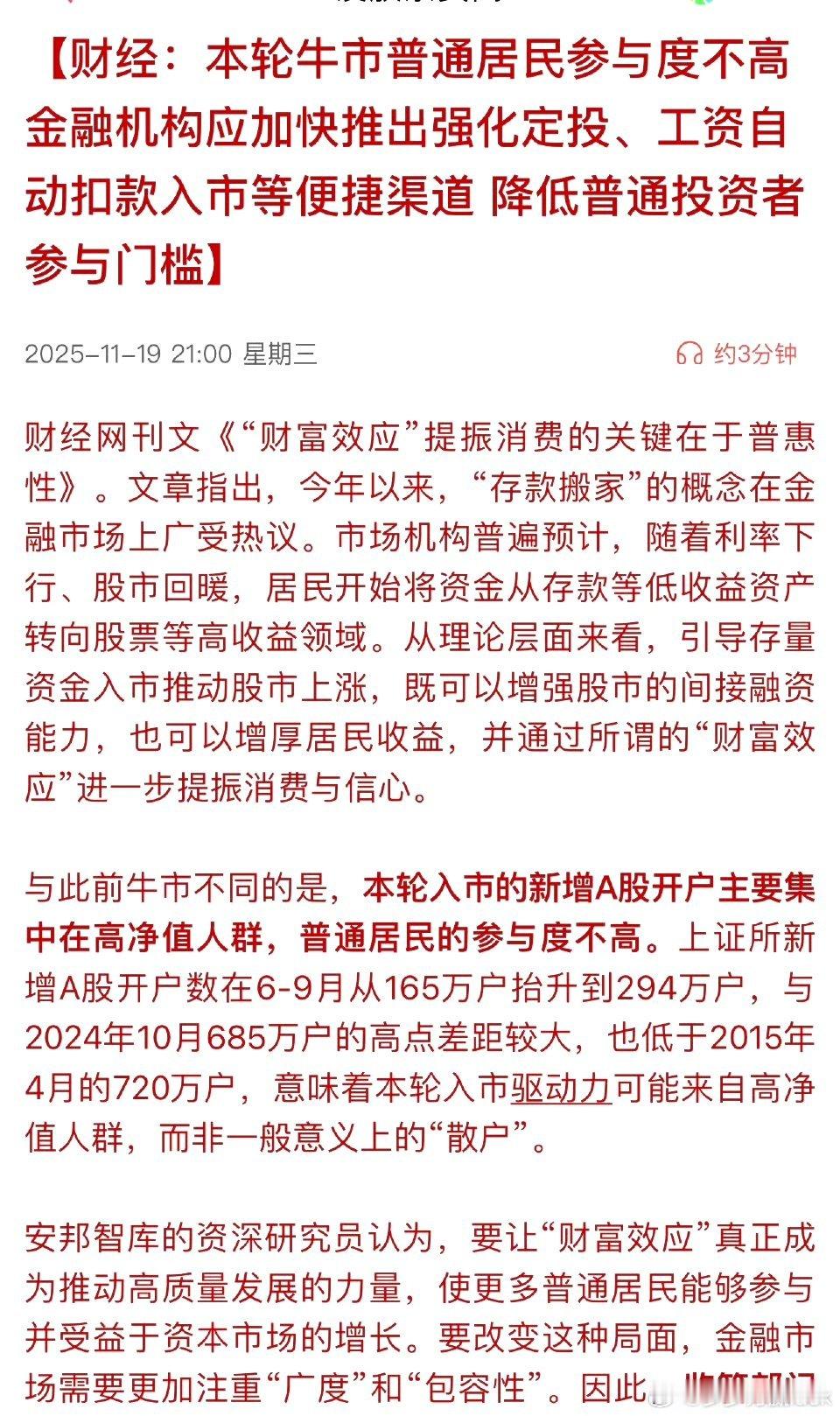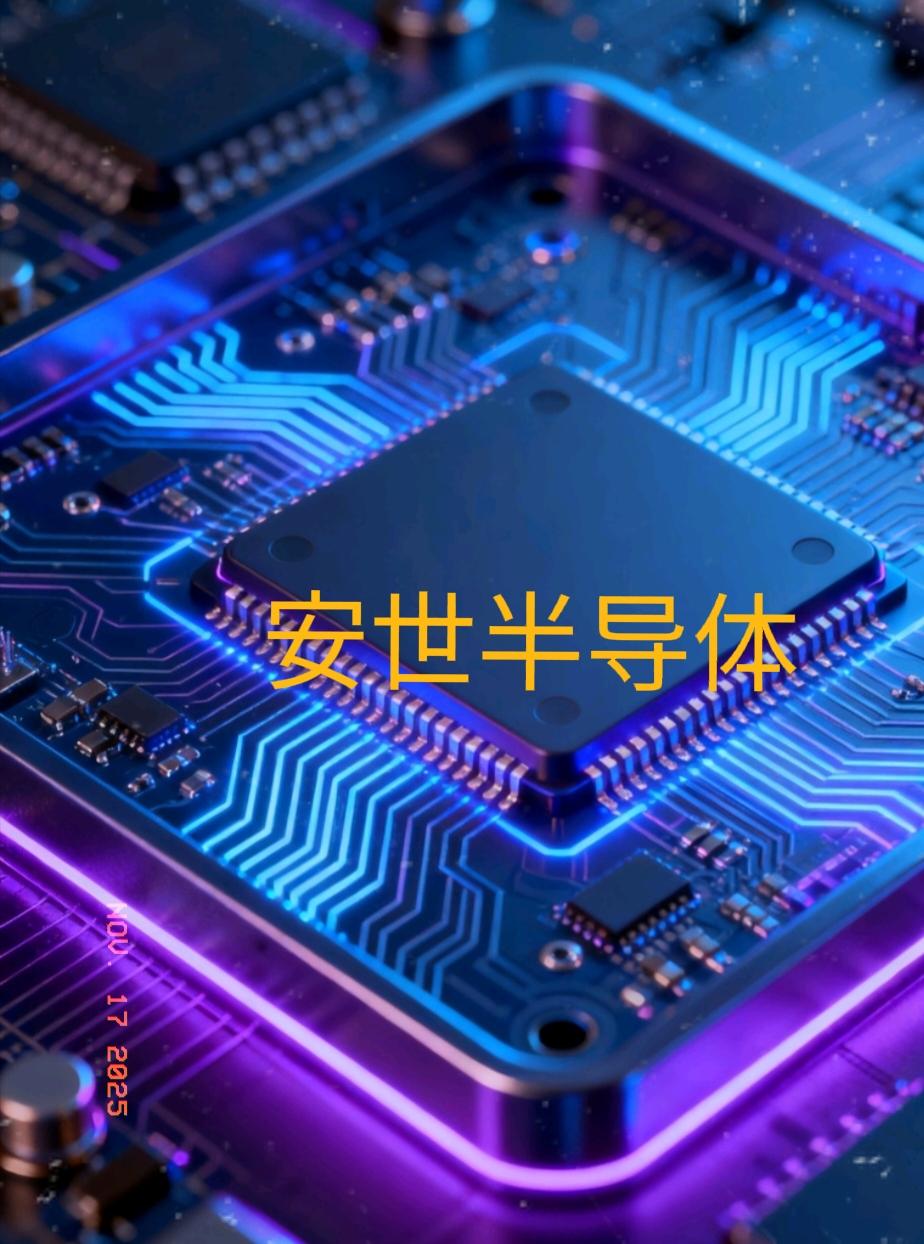9月12日,湖岸生物(即依生生物)正式收到纳斯达克的通知:由于公司普通股收盘价已连续30个交易日低于1美元,不符合上市规则,且不享有任何合规宽限期,其证券将被强制退市。
这纸通知,也为依生生物长达十余年的曲折上市路写下了终章。自2012年纽交所闯关失利、2021年港股冲刺未果后,公司终于在2023年借助与SPAC公司Summit的合并,成功登陆纳斯达克。可惜的是,这场费尽心力组起的资本之局,仅在两年后便黯然收场。
依生生物曾经有很好的基本面。公司核心产品“依生君安”人用狂犬病疫苗已经上市,并凭借其特有的皮卡佐剂技术,打出“更快激发免疫反应”的差异化卖点,一度成为公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此外,管线中还有皮卡重组蛋白新冠疫苗与针对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性疫苗YS-ON-001等在研项目,至少在故事层面颇具想象力。
也正因如此,高翎、海通、奥博乃至后来的海松、康桥等一众知名资本纷纷入局。在他们眼中,依生生物与那些“只烧钱、无收入”的Biotech不同——它有实际产品、有销售渠道,每年还有数亿元营收,看起来“踏实”得多。
即便在退市前,公司最新财报仍显示其营收与净利润双双增长:截至2024年9月30日,收入3.72亿元,同比增长36.2%;归母净利润2057.9万元,翻倍增长。
而退市前,湖岸生物的总市值仅余2584万美元——相较于合并交易前股权价值8.34亿美元,蒸发幅度惊人。
退市是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狂犬疫苗的概念在美国市场上是过时的,即便有利润,如果没有未来新的想象空间,利润不达标的话,美股市场投资人不会看好。“如果在中国大陆或香港上市就会好很多。而后续的投资人判断也不够准确,估值做的太高,自己拿真金白银投进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才亲自下场想要控制公司。”
就在退市前一个月,大股东海松资本联手晶峰投资组成财团,提议以每股0.86美元的价格全现金收购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意图完成对公司的彻底控制。
而另一边,依生生物的创始人,被罢免的前董事长张译并未沉默,他正联合中小股东公开反对收购,呼吁董事会履行信义义务,否决财团提议。一场关于老股东与新资本的拉锯战,在退市的阴影下悄然上演。
控制权,对于一家价值极速缩水的公司来讲,已不仅是利益之争,对创始人张译来说,是“抢回孩子”样的一口气;而对于高价入局的资本方,就像股价高位入局,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摊薄成本。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
-01-
利益分歧

2023年3月底,依生生物还不到半月,股价从10美元下跌到不足2美元。
面对这一波动,在张译的眼中,公司股价暴跌期间,公司基本面并无利空消息,反而是“业绩迅速增长,产品供不应求”,并有新产品完成三期临床等重大利好。因此,他坚信股价异常暴跌是人为做空的结果。
在这一过程中,SPAC基石投资人雪湖资本,在依生生物与SPAC公司完成合并上市后,清仓所持有的非限售185万股,并将本应锁定一年的35万股提前解禁出售。
“上市后就是急速地低价卖,不管价格,只管卖,结果把股价都打下来了。”张译猜测,这一行为可能与后来其他投资方如海松资本的低价增资有关,目的或在于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大的控制权。
但实际上,和张译的理解不一致的是,一位熟悉美股市场的业内人士分析指出,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尤其是一些对冲基金,本质上并非长期股东,而是利用SPAC结构进行短期套利的交易者。他们的投资逻辑不依赖于对并购标的的基本面分析,也不关心公司业务的实际前景。其核心策略在于:在SPAC完成合并时,通过“赎回”机制收回本金,同时保留作为SPAC发行单位一部分的权证,以此实现低风险套利。
因此,这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金融结构套利,而非价值投资。
其实更重要的是,依生生物上市时已错过新冠疫苗风口,其被寄予厚望的皮卡重组蛋白新冠疫苗经历不可避免的价值重估。
股价持续暴跌引发了股东与董事会层面的普遍不安。在2021年B轮融资中出资4000万美元获得4.95%股权的海松资本,作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此时提出追加4000万美元投资,并坚持要求进入董事会,但遭到张译的明确拒绝。
从张译的角度看,海松资本的意图已不仅是降低持股成本,而是进一步谋求公司控制权,这直接触动了他对股权稀释与控制权稳定的警惕。
而站在海松资本的立场,面对股价暴跌带来的巨额账面亏损,他们也难以坐视不管。
双方在融资安排、董事会席位与公司战略方向上的分歧不断加剧,在控制权面前,谁也不愿轻易退让。这场因股价下跌而激化的矛盾,也逐渐从市场层面蔓延至公司治理的核心战场,为后续的控制权之争埋下了伏笔。
-02-
罢免纠纷

依生生物在早前通过借壳上市时,曾从康桥资本获得一笔4000万美元的债权融资。该协议中包含一项关键条款:一旦公司董事长或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立即偿还全部借款。这一条款,在后续的控制权争夺中成为了关键杠杆。
“他们就利用这个先逼我辞职,然后启动股权融资。”
尽管张译仍是公司控股股东,但在董事会中却陷入孤立。2023年12月9日,董事会以5:2的投票结果罢免其董事长职务。
张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该罢免程序违反了公司章程,并已向开曼法院提起诉讼。目前相关司法程序仍在进行中,预计明年将有明确结果。
不过,有分析认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规则中,董事会有权罢免董事会主席。美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创始人CEO被董事会投票罢免的情况并不少见。只要获得足够多数的董事同意,就可以通过决议,罢免董事长或CEO。这类董事会决议投票不涉及股权比例问题,完全取决于董事们的独立表决。
而作为公司创始人及大股东,张译本应在公司融资和股权设计中更加警觉,避免自身股份被过度稀释。
在张译被罢免,触发还款机制后,张译表示,当时公司账面资金已不足以全额还款,而当他寻求其他途径借款时,已被对方控制的董事会却以“必须进行股权融资”为由予以拒绝。
如果张译通过还款而不是股权融资解决问题,那么他会继续掌握控股权,但之所以对方强调股权融资,意图稀释张译的股份,成为大股东。
至此,一场围绕还款条款、董事会席位与融资路径的控制权之争,从制度设计的暗处,彻底走向台前。
理论上,张译作为创始人,在董事长职务被罢免后,仍可凭借其持有过半股份的身份,尝试通过召开股东大会谋求翻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的行动速度可能不够快。
某种程度上,这也源于他过去在公司的强势地位——可能因过于自信而忽视了其他声音,未能及时妥协,导致矛盾激化直至不可收拾。商业决策中,适时让步与平衡各方利益,往往比强硬对抗更能保障长期稳定。
等到融资结束后,张译已经失去了持股比例上的绝对优势,已经无法反击。
-03-
资本,环环相扣

依生生物从创立到衰落的全过程,始终伴随着深刻的资本运作痕迹。
其上市前夕,公司经过一顿操作,通过SPAC合并登陆纳斯达克,在生物科技板块的热潮中市值一度突破10亿美元,透支了市场预期。
然而,SPAC机制本身也对公司造成了结构性伤害。这类交易中,早期投资者多为套利者而非长期股东,一旦完成合并便迅速退出。他们撤离后,留在市场上的往往是看好公司发展的普通散户。若公司基本面未能及时支撑高估值,股价便面临持续压力。这种模式制造了IPO时的短暂繁荣,却在资本离场后留下一片残局。
资本从不沉睡,即便在依生生物陷入困境后,其剩余价值仍被继续挖掘。
罢免创始人张译后,2024年2月,名为“顶峰前景”(ApexProspectLimited)的投资方以4000万美元增资额,按每股0.42美元的价格认购公司约9526.98万股普通股,成为持股52%的最大股东。此次增发导致张译的股权被稀释至26.1%,众多小股东的持股比例也大幅缩水。
张译还揭示了一个关键程序问题:这次股权收购并未经过股东大会批准,而是由董事会直接表决通过。可以说,这次大规模低价增资成为整场控制权争夺的转折点。投资方以极低估值注入资金,一举改变了股权结构与权力平衡,实现了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此后局面越发不可逆转。
与此同时,公司治理与战略方向也引发质疑。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公司后续运营决策几乎完全围绕“削减成本”展开,逐渐偏离原有发展方向,湖岸生物连基本面也逐步丧失。
为维持上市地位,2024年10月,公司进行10:1反向股票分割。这一操作最直接的目的,是应对纳斯达克对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的退市警告。理论上,并股可将股价提升十倍,是典型的“续命”手段。然而在极低股价下进行融资,公司需发行大量新股,严重稀释现有股东权益。因此,这次并股也被视为是为后续定向增发打下可操作的股价基础,甚至进一步改变控制权格局。
果不其然,2025年7月8日,公司再次向晶峰投资(CrystalPeakInvestmentInc.)进行定向增发,普通股发行价为0.883美元/股,认股权证定价1.079美元/股。交易完成后,晶峰投资持有公司约51%股权。
2025年8月,海松资本联合晶峰投资等组成的财团提出以每股0.86美元收购湖岸生物剩余股份的提议,若通过将实现对公司的彻底控制。
“外界可能一度低估了海松资本。他们最初或许未被视作主导力量,但其为保全投资、夺取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相当果决。如今他们提出极低报价,意图全额收购所有流通股。”
在一个投资机构人士看来:“海松是无奈,为了自救,必须下场”。
“一些更大的资本,拥有更强的资源,为了构筑生态圈,会主动并购、孵化企业(当然效果不一定好),如果不是怕自己的资本缩水,收不回来,海松这个体量不算大的基金是不愿意下场的。”上述人士表示。
但一旦下场并掌握控制权,就会全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张译和其它小股东方将处在被动的地位。
至此,这场始于资本入场、终于资本控局的博弈,已几乎再无回旋余地。
-04-
雪崩在前

如今依生生物已经退市,根据资本市场规则,一旦退市,持股占绝对多数的大股东便可以启动程序,强行收购少数股东的股份。而令张译愤慨的是,海松资本提出的收购价格,仅为股东初始投资价值的约1/100。
如今为了捍卫自身与其他小股东的权益,张译已在境外对公司董事会及海松资本等相关方提起了诉讼,指控其在罢免程序及增发交易中存在违法行为。案件预计在明年开庭。然而,他正身处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之中——海松资本极有可能在诉讼结果出炉前,就完成私有化交易。
谈及诉讼目标,张译表示:“我的预期就是纠正他们董事会的非法行为,恢复到原状。责任方必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并追究其赔偿责任。”
为增加胜算,张译及其代表的小股东群体已向海松资本发出律师函,明确警告其若强行推进私有化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
依生生物的兴衰,是药企与资本从共生走向决裂的缩影。他们在公司走势上扬时,利益一致,一荣俱荣。当市场退潮、基本面未达预期时,资本反噬,公司暴露于狙击风险之下。依生生物的结局,将为行业带来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长久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