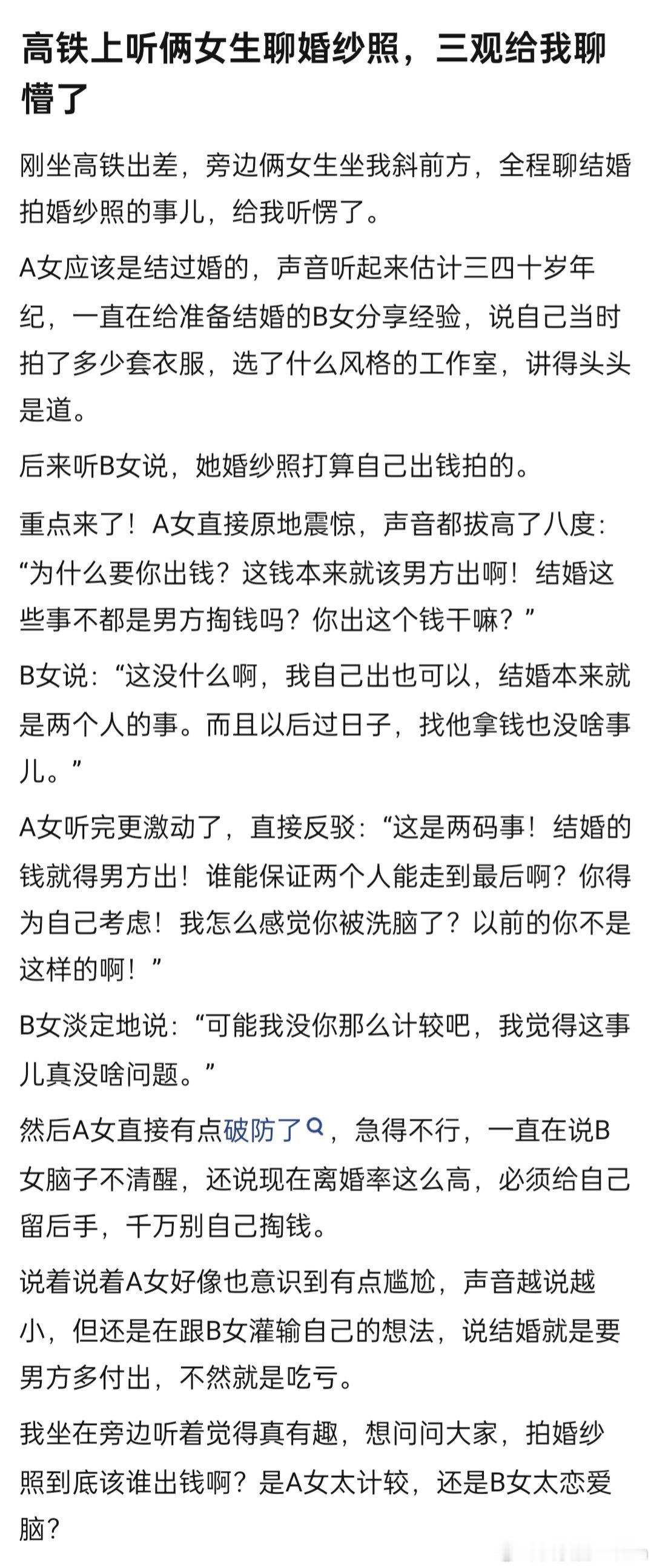大妈上了高铁,发现一小伙坐了自己位置,她上前说:小伙,我不认识字,帮我看看我位在哪。小伙仔细看了看说:阿姨,您这是站票,站哪都行。 大妈的手没从靠背上拿开,反而攥得更紧了。头顶的空调口嘶嘶地吐着冷气,她胳膊上的鸡皮疙瘩一直没消下去。布包带子深深勒进她粗糙的手心里,那包里好像装着很实在的东西,坠得包底都变了形。 “我儿子……不会买错的。”她声音更低了,眼睛却一直盯着那靠窗的座位,仿佛那是个必须抵达的终点。 小伙低头又划拉了几下手机,没再说话。过道里人来人往,大妈被挤得微微晃动,像棵站久了有点乏的树。她终于松开了攥着靠背的手,慢慢蹲下身,把那个沉甸甸的布包搁在脚边,人就靠着座椅的侧面,蜷缩下来。 小伙瞥见她花白的头发顶,和那只放在布包上、布满老茧和细小裂口的手。手背上有一道挺深的旧疤。车厢广播报站,声音清脆。小伙忽然把腿收了收,身子往窗边使劲贴了贴,空出大半个座位。 “阿姨,您坐吧,我……我坐累了,想站会儿。” 大妈抬起头,眼神有点发懵,看了看空位,又看了看小伙。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然后才用手撑着座椅,有些吃力地站了起来,慢慢坐下。布包被她紧紧抱在怀里。 她坐下后,也没道谢,只是默默地从那个旧布包最里头,掏出一个裹了好几层塑料袋的铝饭盒。打开,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韭菜盒子,还冒着一点温热的气。她拿起一个,递给旁边站着的小伙。油很快渗过塑料袋,沾到她和他手上。 “自己做的,干净。”她就说了这么一句。 小伙接过来,咬了一口。很家常的味道,韭菜鸡蛋馅,咸淡正好。大妈自己也拿了一个,小口吃着,眼睛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模糊田野。 “去看儿子?”小伙问。 “嗯。”大妈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才补充,“给他送点吃的。他干活的地方,饭贵。” 小伙没再问。他吃完韭菜盒子,把塑料袋仔细折好。车慢了下来,又要到一个站了。他伸手从行李架上拿下自己的背包。 “阿姨,我到了。” 大妈点点头,看着他。小伙走到车厢连接处,又回头看了一眼。大妈已经挪到了他刚才让出来的靠窗位置,侧着脸望向窗外。那个旧布包放在旁边的空座位上,占去了大半,又好像特意留出了一小块地方。 车停了,又开动。窗外的光斜照进来,落在那个空座位上,亮堂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