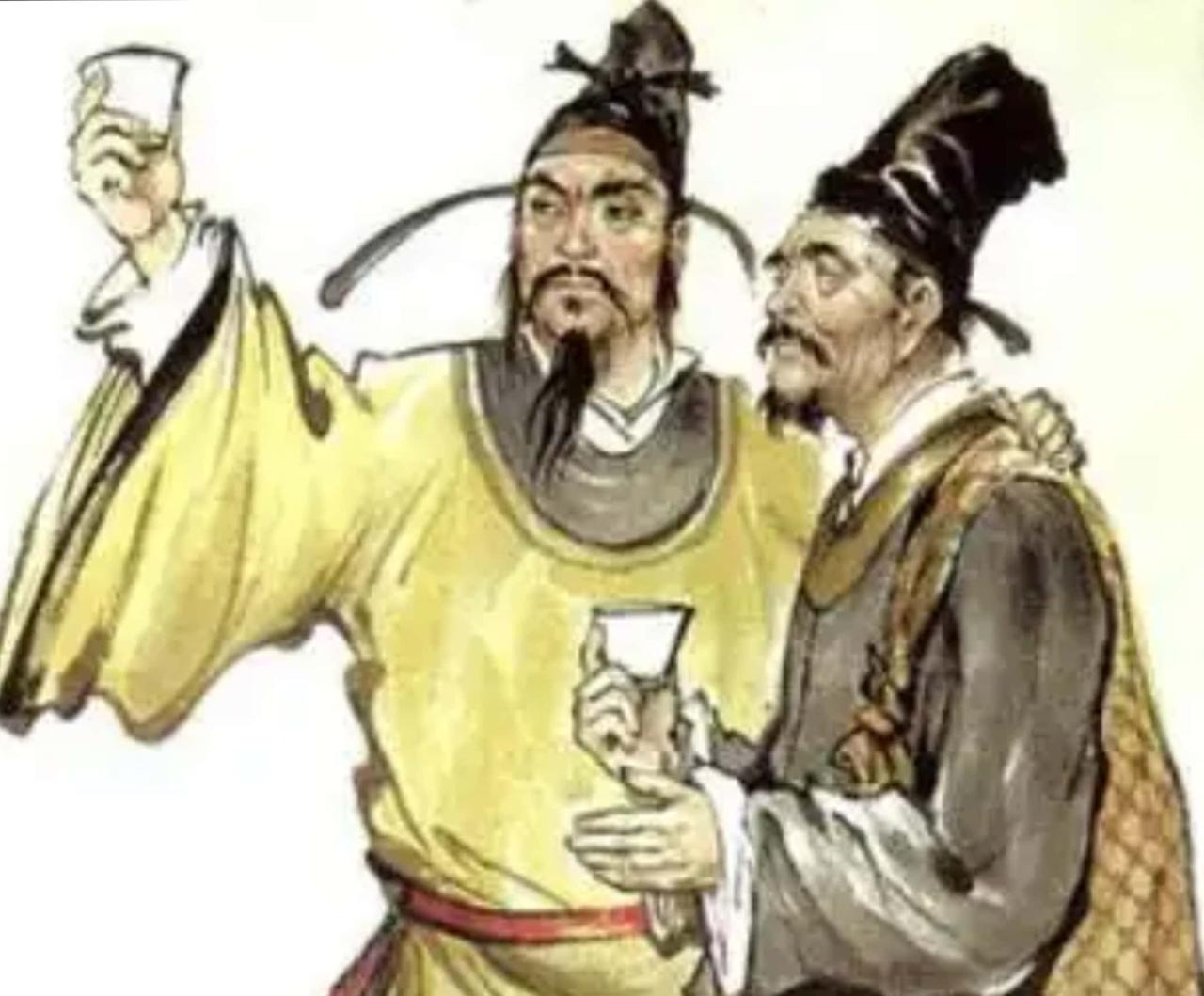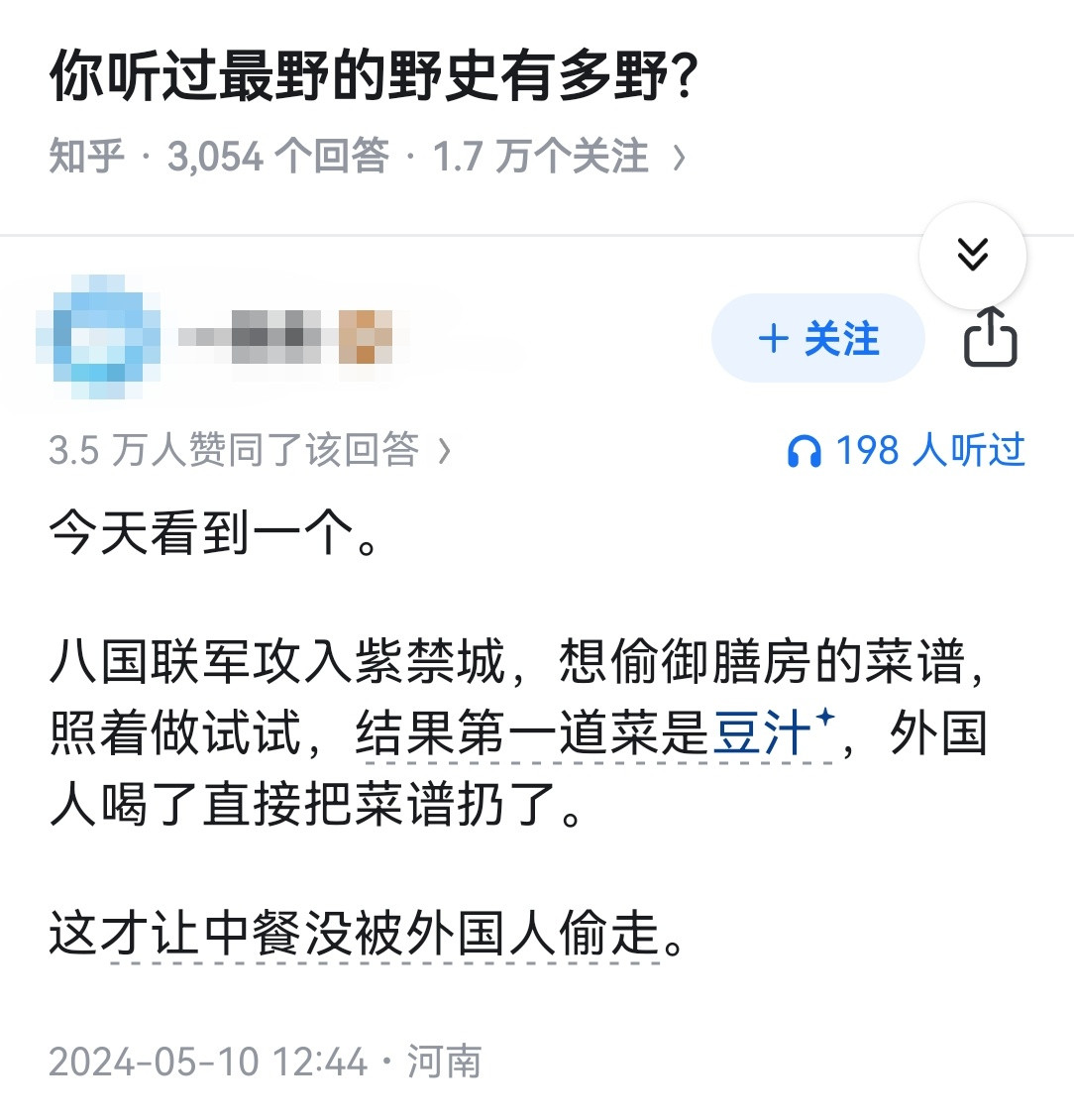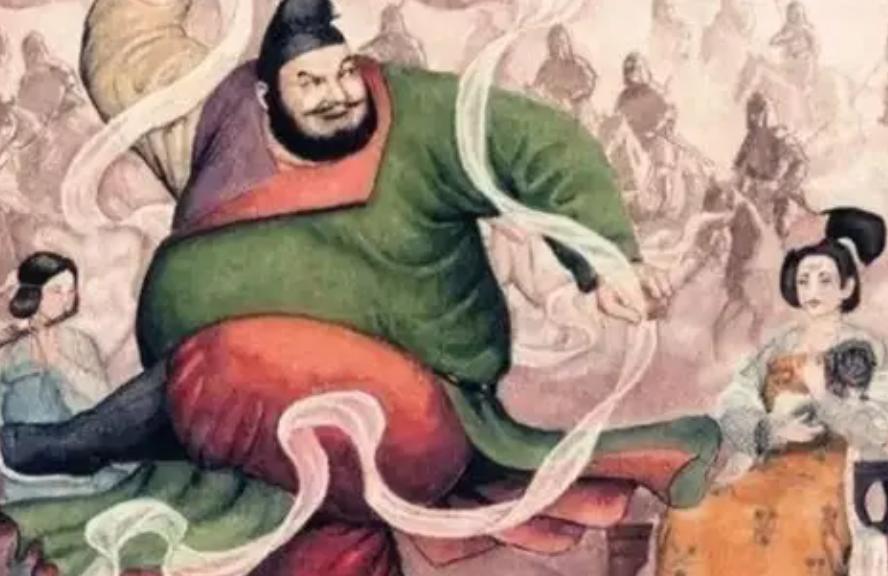今天咱们不聊那些金戈铁马的开国皇帝,也不聊那些运筹帷幄的千古名相,咱们来聊一个职场奇迹,一个在五代十国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年代里,活成了“不倒翁”的男人——冯道。
如果把五代十国比作一个频繁破产重组的集团公司,那冯道绝对是史上最牛的“行政总监”。他这一辈子,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如果算上中间那些短命的政权和偶尔向契丹称臣的时刻,理论上他一共伺候过6个朝代、12位皇帝。
更离谱的是,不管董事长的位置上坐的是谁,姓李、姓石、姓刘还是姓郭,甚至姓耶律,冯道总能稳稳地坐在宰相、太师这些核心高管的位置上。
有人说他是政坛常青树,有人说他是王朝送终机——毕竟谁得到了冯道,离公司倒闭也不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流水的皇帝,铁打的冯道以此人的经历,如果放在现代职场,大概是这样的剧本:
冯道在A公司当总监,业务能力极强。结果A公司被B公司收购了,老板换了,冯道没动,继续当总监;没过两年,C公司又把B公司吞并了,冯道还是坐在那个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后来D公司、E公司轮番上阵,连外资企业(契丹)进来托管了一阵子,冯道依然是那个雷打不动的总监。
在咱们外人看来,这人是不是心思太活络了?毫无忠诚度可言,跳槽比换衣服还勤快。
但你站在冯道的视角看,其实挺冤枉。他压根就没跳槽,他一直就在那儿正常打卡上下班,架不住公司倒闭得太快,老板换得比走马灯还勤。他有什么办法?
冯道不仅能混,而且业务能力极强。他做了一件让后世所有读书人都得磕头感谢的大事:主持刻印了《九经》。
在冯道之前,书是靠手抄的,错别字连篇,还容易丢。冯道利用职务之便,搞了一个国家级的“文化工程”,历时22年,把儒家经典全部雕版印刷,标准化了。这相当于给华夏文明做了一个云备份。后来沈括都说,从冯道之后,咱们才真正进入了印刷时代。
就凭这一条,当时的人评价他“与孔子同寿”,是德高望重的社稷元老。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对冯道的评价开始出现了一个极其有趣的两极反转。这哪里是评冯道,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士大夫心理变迁史”。
一场跨越千年的“口水战”冯道活着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好,是因为乱世之中,能活下来且给老百姓办点实事不容易。
但到了北宋,风向变了。
欧阳修骂他“无廉耻”,司马光更是气得在《资治通鉴》里把他定性为“奸臣之尤”。宋仁宗甚至对着冯道的后人骂:你太爷爷是个无节操的小人,你还有脸来我要官?
为什么?因为屁股决定脑袋。
北宋建立初期,为了确立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强调“忠君”。如果大家都学冯道,宋朝皇帝哪天被推翻了,大臣们是不是也直接转头伺候新主子?那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欧阳修和司马光骂冯道,其实是在给宋朝的官员立规矩:你们得死忠,不能学那个老滑头。
好玩的是,到了王安石这儿,他又把冯道夸了一通,说他像“佛菩萨”。为啥?因为王安石是变法派,跟司马光这帮保守派死对头,凡是司马光反对的,王安石大概率就要支持一下,而且王安石更看重实绩。
再往后,到了明朝中叶,李治(不是唐高宗那个李治,是明朝学者)又出来给冯道点赞。他说五代那种乱世,老百姓能少受点苦,全靠冯道在中间周旋。
可等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又跳出来,把冯道踩到了泥里,说他比奸臣还坏。这又是为什么?因为王夫之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最恨那些投降清朝的汉臣(比如洪承畴、钱谦义)。他骂冯道,其实是在指桑骂槐,骂他同时代那些没骨头的软蛋。
你看,历史评价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客观事实,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往往是评价者自己所处的时代焦虑。
第三条路:苟且还是救赎?到了现代,关于冯道的争论依然没停。学者葛剑雄和方文曾有过一场精彩的交锋。
葛剑雄老师提出了一个“第三条路”的观点。
在五代那种极度混乱、君主像走马灯、且多是暴君杀人狂的年代,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
第一条路:学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或者自杀殉国。可五代50年换了6个朝代,如果都要死节,那得自杀十几次,显然不现实。 第二条路:隐居山林。但这在乱世很难,而且等于把天下拱手让给流氓和军阀,老百姓更惨。 第三条路:就是冯道走的路。在这个烂透了的体制里,尽量保全自己,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保存文化的火种。
葛老师认为,冯道是为了苍生,忍辱负重,这比那些愚忠的人更伟大。
但方文先生坚决反对。他认为,这纯粹是洗白。
方先生觉得,冯道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说他是为了百姓?他在契丹人打进来的时候,对着耶律德光称臣,这难道不是汉奸行为?难道当了亡国奴、做了儿皇帝的帮凶,还能说是为了百姓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贪生怕死、贪恋权位。
这两位神仙打架,其实各有道理。
葛老师看重的是“民生”,在乱世中,活着并做事是第一位的;方先生看重的是“气节”和“大义”,原则问题不能退让。
樗散生的小总结听完这些争论,我们该怎么看冯道?
其实,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视角,也就是“后人视角”,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站在时间轴的高处往下看。
当社会稳定、国家自信的时候(比如明中叶、清乾隆),人们往往对冯道比较宽容,觉得他关注民生,是个好官。因为这时候没有亡国的危险,大家更在乎日子过得好不好。
当社会动荡、外族入侵、或者政权合法性需要强化的时候(比如宋初、明末清初、民国),冯道就会被拉出来鞭尸。因为这时候,忠诚和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痛恨背叛。
冯道本人,其实就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下,试图在“个人生存”和“职业理想”之间寻找平衡的普通人。他肯定不是圣人,他有私心,想保住荣华富贵;但他也不是纯粹的小人,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文脉,劝谏了暴君,少杀了不少人。
他就像那个在公司频繁被收购、裁员的大潮中,依然坚持每天早起打卡、把项目推进下去的中层干部。虽然显得油滑,虽然不够热血,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公司倒闭的时候,那个核心的数据库才没有被格式化。
历史往往不给我们提供标准答案,只提供样本。冯道就是那个最复杂的样本,提醒我们:在黑与白之间,还有一片巨大的、灰色的、但也充满了真实人性的中间地带。
我们不必急着去崇拜他,也不必急着去唾弃他。在那个把人变成鬼的乱世里,他努力让自己像个人一样活着,这本身,或许就已经是一种不仅限于道德的生存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