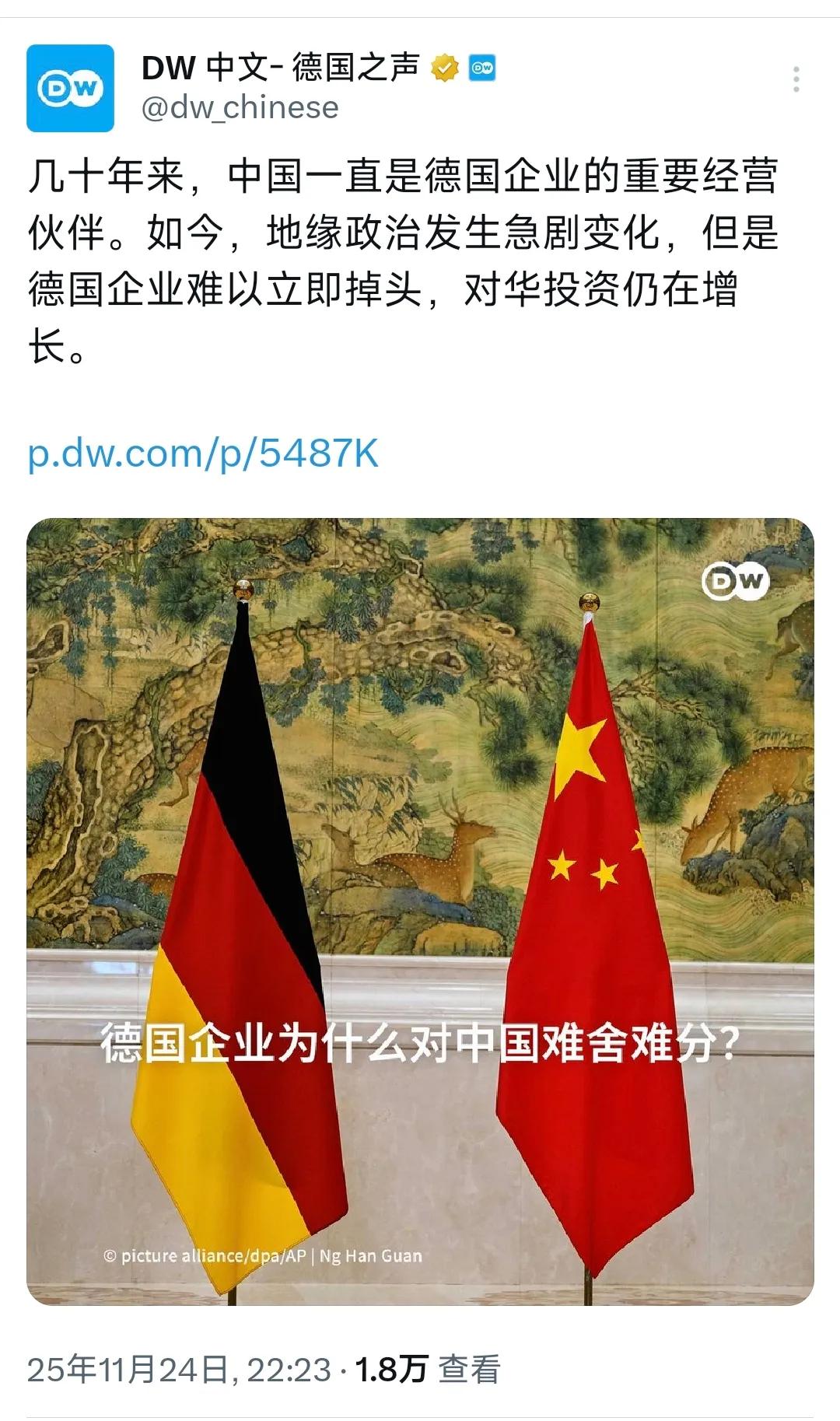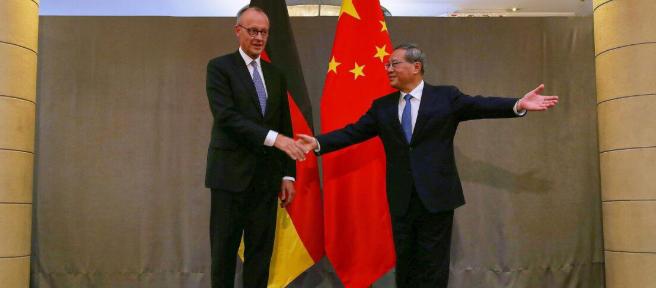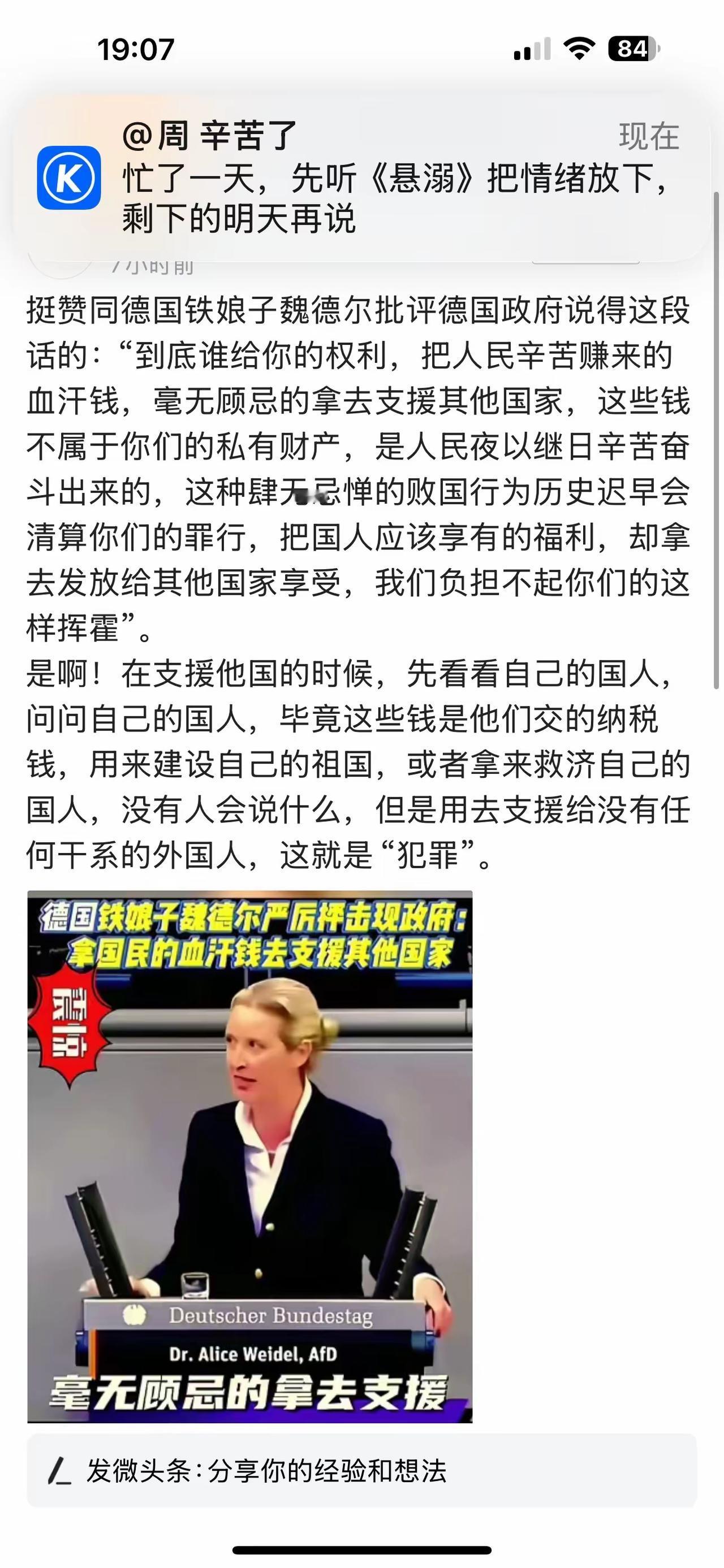德国地方财政的裂缝已经演变成无底洞,从柏林到小城镇,市政厅的预算文件上写满了同一个词:破产。
埃森市市长托马斯·库芬的警告令人不寒而栗:“几乎每一座德国城市都处在破产边缘。”这位市长面对的不是短期资金短缺,而是德国地方政府全面崩盘的财政系统。
在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396个城镇中仅有10个还能维持预算平衡,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揭示了德国地方财政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当前德国各城市及市政当局的累计预算赤字已攀升至300亿欧元,这一数字在2024年还为240亿欧元,创下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高纪录。

01 财政灾难的规模与分布
德国首都柏林成为赤字“重灾区”,赤字规模高达43亿欧元。科隆以6亿欧元赤字紧随其后,杜塞尔多夫则以4亿欧元赤字位列第三。
汉堡、慕尼黑等多个经济重镇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财政缺口,地方财政危机已呈现“全面蔓延”态势。
这场危机在德国是普遍存在的。埃森市市长库芬指出无论城市位于北部、南部、东部还是西部,情况都一样严峻。他透露预算冻结现在“无处不在”,甚至包括许多以前富裕的城市。
财政压力反映在公共服务削减的现实困境中。以柏林为例,当地教育部门已透露,部分公立学校的课外活动经费可能被压缩,青少年中心的开放时间或将缩短。科隆市文化局则表示,若财政状况无改善,明年部分中小型博物馆可能面临临时闭馆或减少展览场次的风险。
甚至传统的圣诞树装饰也成为削减对象,彰显出德国财政困境已触及日常生活各个角落。
02 收入下滑与支出激增的双重挤压
德国地方财政危机并非偶然,而是系统性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矛盾的核心在于 “收入端下滑”与“支出端激增”的双重挤压。
在收入方面,德国工业领域的持续低迷直接导致地方税收锐减。作为欧洲工业核心国,德国汽车、机械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近年面临能源成本高企、全球需求疲软等多重挑战。
企业盈利能力下降,进而影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地方核心税源。数据显示,德国地方税收收入连续多个季度呈负增长,其中贸易税收入几乎停滞,2025年上半年仅增长0.4%。
相比之下支出压力更为突出。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及能源危机后续影响发酵,社会福利相关支出持续攀升。
2025年上半年,德国各地区社会福利支出增长6.4%,达到445亿欧元;人员支出增长6.3%,达到520亿欧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利息支出激增近19%,达到21亿欧元,凸显债务负担加剧。
埃森市市长库芬指出,激增的社会支出包括教育援助、难民安置及融合费用,而联邦和州政府将这些任务转移给城市时,资金支持却不足。

03 经济模式的结构性问题
德国财政危机深层次反映了其经济模式的结构性问题。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导向和制造业,当全球贸易格局变化,这种模式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德国汽车行业正陷入困境,痛苦正在蔓延。作为德国经济核心的汽车产业面临严峻挑战,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舍弗勒计划裁员700人,另一家供应商采埃孚则计划裁减1.4万个岗位。
德国金属工会甚至警告,德国中部工业区可能面临数千个工作岗位的削减。
这些工业衰退直接影响地方财政。因戈尔施塔特市长沙普夫正在应对近1亿欧元的财政缺口,而这主要源于当地支柱企业奥迪公司的衰退。奥迪每年通过母公司大众汽车向市政府贡献的超过1亿欧元税收已经枯竭。
更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在软件和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投资滞后。2022年德国研发投资占GDP的3.1%,而美国为3.6%,韩国达5.2%。数十年的政府投资不足导致德国基础设施衰退,商业研究机构估计德国未来十年需要投入6000亿欧元弥补投资缺口。
04 联邦政府的回应与局限性
面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困境,德国地方政府已开始向联邦政府寻求支持。据报道,德国13个联邦州的州长已联合向总理默茨提交援助请求,呼吁联邦政府出台针对性政策。
默茨政府已对地方财政危机作出初步回应。总理本人公开承认,市政当局正面临“极其严重的财政问题”,并呼吁地方政府“更加谨慎地使用资金”,在开支方面推行“精细化管理”。
联邦财政部透露,目前正研究通过转移支付、低息贷款等方式为地方政府提供流动性支持。
然而这些措施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以埃森市为例,库芬市长表示,联邦政府的债务援助计划在未来十二年内仅能提供3.35亿欧元,平均每年仅2800万欧元。由于建筑成本飙升,这笔钱“运气好的话也只够建两所半学校”。
更严峻的是,联邦政府自身的财政状况也不容乐观。联邦审计法院对政府2026年预算的审查结果显示,预计明年近三分之一的支出将以信贷方式进行。
审计人员尖锐指出,联邦政府“结构性地入不敷出,已无法依靠自身收入可持续地为核心政府职能提供资金”。
05 解决路径与未来展望
解决德国地方财政危机需要“短期纾困”与“长期改革”相结合。短期内,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与政策倾斜能缓解地方流动性压力,避免公共服务大规模缩水。
但从长期来看,核心在于构建可持续的地方财政体系。这需要德国在推动工业复苏以提振税源的同时,优化地方财政收支结构,例如通过完善财税分成制度、合理控制福利支出增速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收支失衡问题。
地方政府也在主动探索自救措施。埃森市已启动“财政节流计划”,通过合并行政部门、优化公共服务流程降低行政成本;柏林则计划通过盘活城市闲置资产、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公共项目等方式拓宽收入渠道。
然而更深层次的改革可能触及德国财政体系的核心规则。埃森市市长库芬呼吁:“我们需要讨论如何防止我们的福利国家变成一个需要福利救济的国家。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想负担得起什么,我们还能负担得起什么?”

他进一步指出关键不仅在于资金,更在于减少官僚主义、简化审批流程,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德国联邦审计法院的警告声犹在耳畔:到2029年,德国近八分之一的税款可能都要用于支付利息。联邦政府目前背负着1.9万亿欧元的债务,而2020年这一数字还仅为1.3万亿欧元。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博弈也在加剧。13个联邦州的州长已联合向默茨提出援助请求,而州长们则要求联邦政府为“投资助推器”政策带来的地方财政损失提供补偿。
这场财政危机不仅关乎数字,更关乎民主制度本身。正如埃森市长库芬所强调的,“民主是在市政厅里被捍卫的”。当市民发现幼儿园申请不到位置、夜晚路灯不再亮起时,对政府的信任也将随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