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里带着汴梁城初春的柳絮,元祐初年的某个午后,苏轼坐在翰林院的案前,手边是刚送来的墨香纸卷,窗外有鸟叫,屋里却静得只听见笔尖蹭过纸的声音。他要写的,不是奏章,不是诗,而是一篇给王安石的追赠制词。
你可能不知道,这俩人在政坛上互撕了半辈子。一个推新法想让国家富得流油,一个骂新法把百姓逼得跳脚。按常理,老苏这时候就该顺手黑一把,踩两脚,给旧党立威吧?
可他没。不但没黑,还写得挺客气,甚至有点……敬意。
说白了,这事乍看反常识:号称“北宋嘴炮双雄”的两位大佬,斗得你死我活,输赢都写在朝堂上,怎么人走了,反倒送上一份体面?
我猜啊,这里面的弯弯绕,比新法的条文还复杂。
先岔开说个小场景
我总觉得,王安石这人吧,活着的时候像一杯烈酒,够劲,但也烧心。年轻时的他,挑灯夜读,眼睛熬得通红,心里就一个念头:大宋积弱,不改不行。后来当了宰相,推青苗法、募役法,一刀下去,有人发财,有人破产。苏轼呢,典型的“稳字派”,觉得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裆。两人在朝堂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旁人看得津津有味,跟看相声似的——只不过包袱里夹着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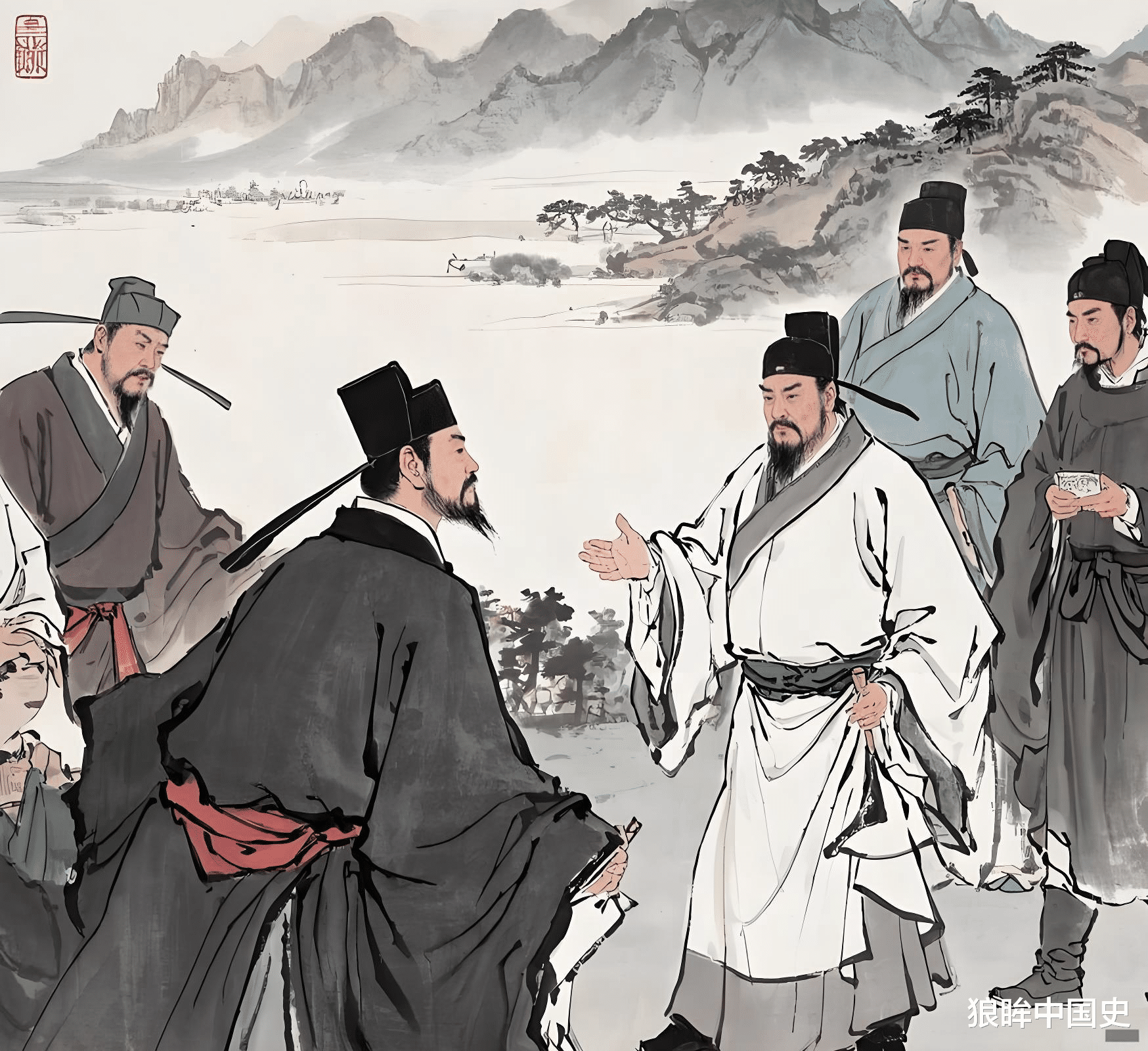
有一次,坊间还传,王相公当面怼苏学士:“子瞻(苏轼字)文章妙天下,可惜不懂实务。”苏轼回得也绝:“介甫(王安石字)经术通天人,可惜不近人情。”
你看,火药味隔着百年都能闻到。
回到那个午后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旧党掌权,司马光一派春风得意。按理说,这是个绝佳的“清算时刻”,把新党代表人物批倒批臭,祭旗都行。可奇怪的是,朝廷照样给他追赠太傅,还让苏轼执笔写制词。
为啥?
我觉着,首先是礼制摆在那儿。宋代翰林学士写这种官方追赠文,是职务活儿,不能任性撂挑子。其次嘛,政治空气也需要一点“体面”。你要是这时候把死人往死里踩,外人看了会说:旧党心胸狭窄,只会胜则骄败则辱。对自个儿名声不好。
再说,苏轼这个人,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的脾气。他跟王安石吵归吵,心里是有佩服的——王的那股子改革狠劲,还有学问底子,真不是盖的。苏轼自己说过,“吾与介甫,出处虽异,其志未尝不同。”意思就是:咱俩走的路不一样,但想让国家好的心,是一样的。
笔下的分寸感
这篇制词,现在还能读到。苏轼夸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好刑名”,意思是早年浸淫儒学,后来钻研法治经济,眼界广。接着又说他的新法“用意良苦”,只是执行出了岔子。你看,这话就有水平——功劳给了,毛病也点了,但不带脏字。
说实话,这种写法挺冒险的。旧党里有些激进派读了,估计心里嘀咕:老苏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可苏轼不怕,因为他知道,留一段平实的记录,比一味骂战更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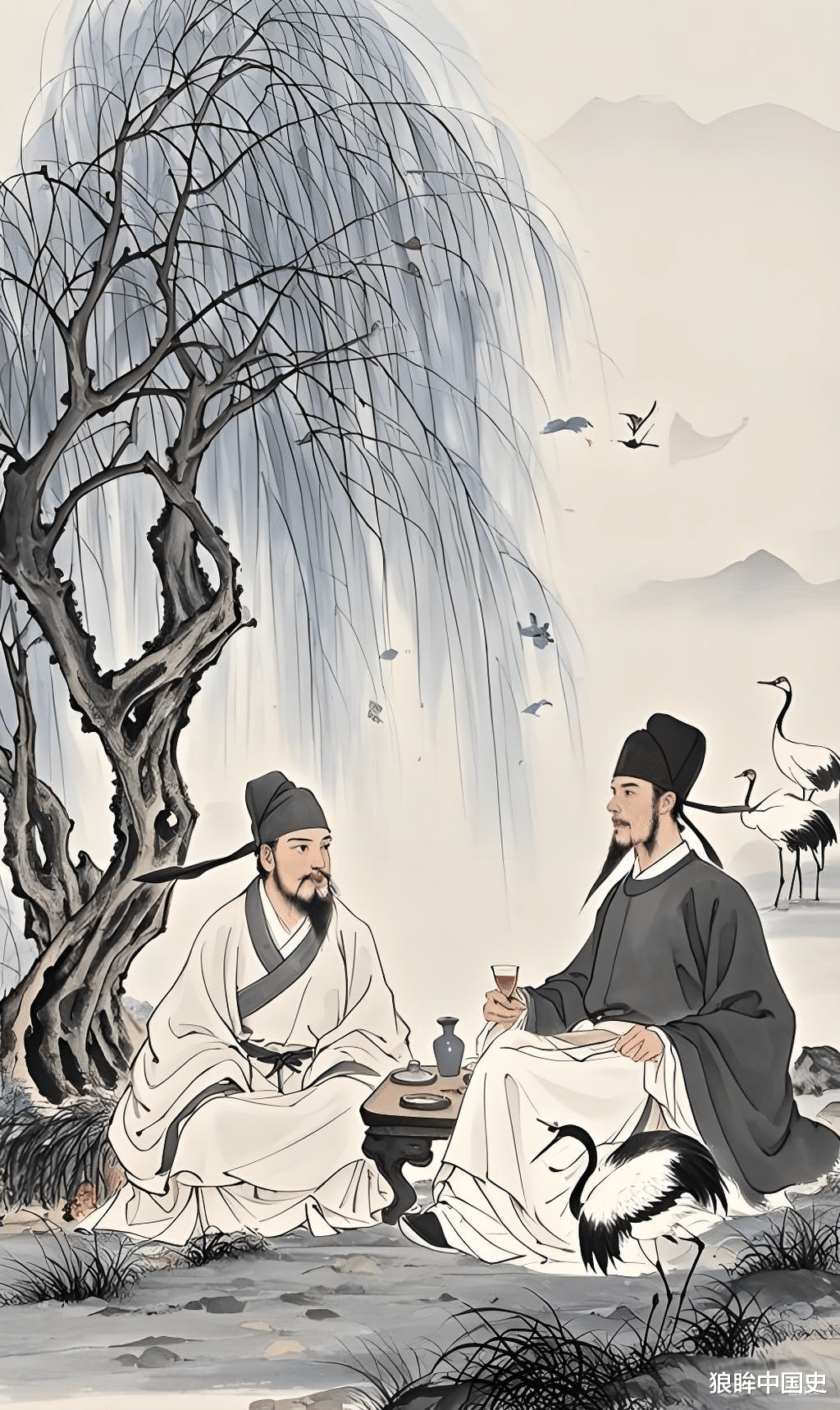
我还想象一个小画面:苏轼写完最后一个字,搁笔,端起茶喝了一口,皱皱眉,嘀咕一句:“唉,这人呐,做事太急,做人倒真有几分孤忠。”——纯属我编的哈,但我觉得,挺像他会说的。
换个角度想
你要站在王安石家人的立场,请苏轼写这篇东西,其实也是精明。苏轼是谁?文坛顶流,声望高,说话有分量。他要是笔下留情,老王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不至于全黑。反过来,如果苏轼一口一个“奸佞误国”,那王家脸上也无光。
而从苏轼的角度,这活儿接得值。一来显气度,二来立口碑,三来——咱别忘了——他也是要写史的人,手里的笔,能决定很多人百年后的模样。
这就像今天职场里,有时候对手离职甚至退休,你写推荐信或者回顾,是往死里损,还是实事求是加点肯定?损了,人家背后笑你格局小;肯定了,别人觉得你厚道。苏轼选了后者,而且做得不卑不亢。
情绪转个弯
写到这儿,我本来还想吐槽一句“北宋官场真会演”,但想想又觉得,这不是演,是某种底线。哪怕党争成那样,他们依旧守着“死者为大”“笔下有德”的古训。你说这算虚伪吗?我倒觉得,这是一种很人性的克制——不把恨延伸到坟墓那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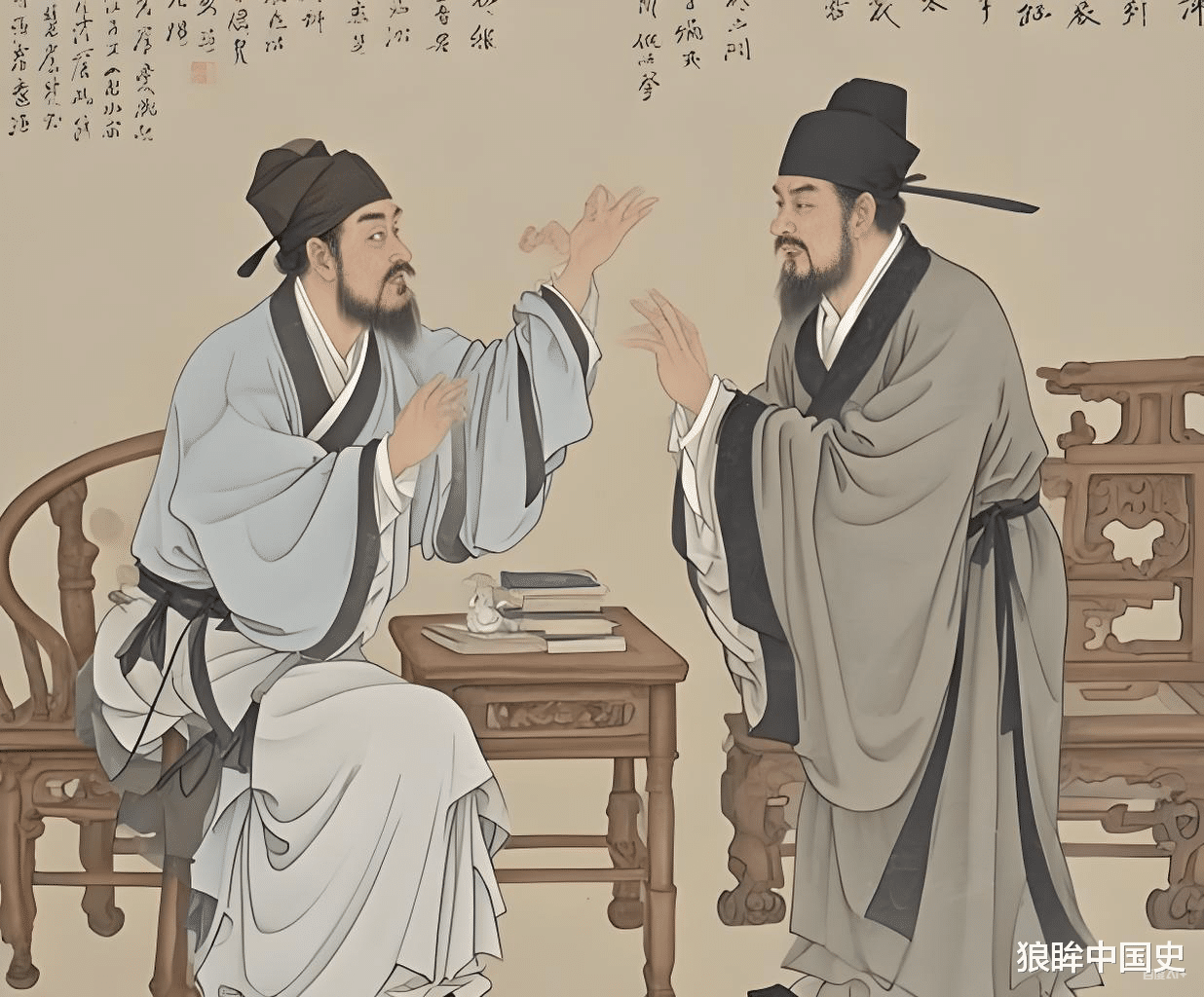
历史的有意思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好坏二分。王安石的急进,的确让不少百姓吃了苦;可他的出发点,不是贪权,是真想改掉国家的积弊。苏轼的温和批评,也不是怕事,是不想把改革与人格混为一谈。两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这个国,只是路线不同。
拉回眼前
我们现在看这段事,可能觉得离得远。但其实挺像职场或生活里的某些场景——你和某人因为理念不合吵得天翻地覆,甚至成了彼此眼里的“死对头”。可有天对方离开了,你愿不愿意在别人面前说句公道话?敢不敢承认对方也曾认真努力过?
苏轼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可以争,可以不认同,但落笔时,留一分对人的基本尊重。
历史不会重复细节,但会重复逻辑——那就是,极端对立容易毁掉判断,而适度的体谅,能让故事多一层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