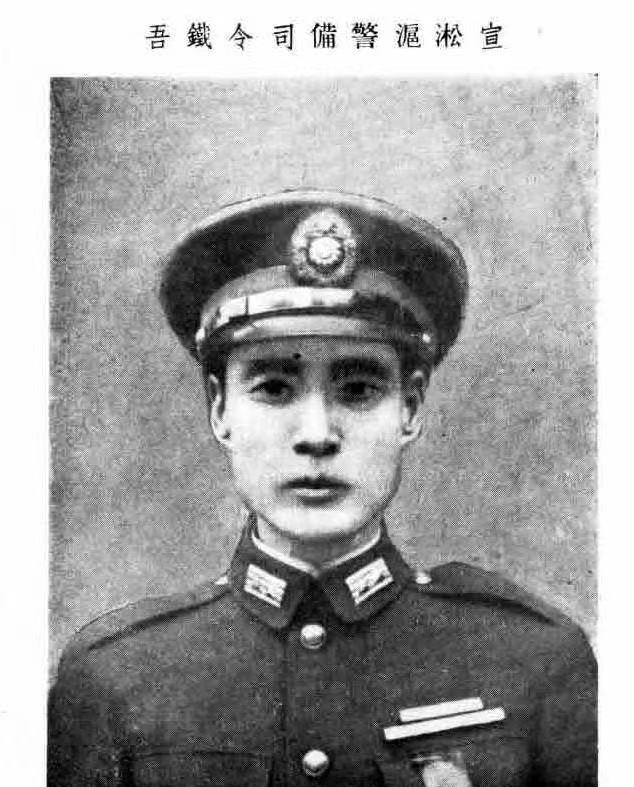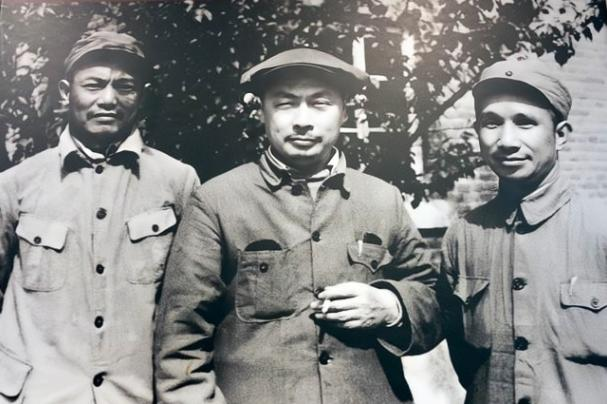1939年,东北一女地下党被日军抓捕,因承受不住鬼子的酷刑,她大喊说:“太君别打了,我全招!"鬼子得意忘形地说:“早知如此,就不用受皮肉之苦了!“可最后鬼子却后悔了.... 那年的东北大地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下,抗日烽火在这片黑土地上持续燃烧,在这片敌占区的暗流中,活跃着无数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 在辽宁某个小县城里,有个穿着补丁棉袄的年轻妇女,每天挎着竹篮在街巷叫卖针头线脑,谁也没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商贩,竟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重要联络员。 田仲礁自从加入党组织后,便以走街串巷的小买卖为掩护,她总把情报卷成细条塞进发髻的木簪里,遇到盘查时就故意把针线撒得满地都是。 腊月里寒风刺骨,她裹着露棉絮的旧袄子,踩着冻硬的土路往返于县城与郊外,鞋底磨穿就垫上干草继续走。 这份工作看似平常,实则需要异于常人的警觉——每次经过日军岗哨,她都要提前两里地绕路;遇到伪军查货,得故意把针线包抖落得七零八落。 这年深秋,田仲礁照例挎着竹篮往城西去,刚转过街角,突然从巷子里冲出七八个持枪的日本宪兵。 带头的军曹举着张泛黄的照片,对着她的脸反复比对,田仲礁心头一紧,手指悄悄摸向发髻里的木簪,却发现四周早已被堵得水泄不通。 直到被押上囚车时,她还在困惑:自己每次传递情报前都会绕三遍路,接头时总要确认三次暗号,究竟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关东军特高课的审讯室里,烧红的烙铁在铁盆里滋滋作响,审讯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出的每个问题,都像尖刀戳在田仲礁的神经上。 她的十指被竹签刺得血肉模糊,辣椒水灌得鼻腔火辣辣地疼,但始终紧咬着渗血的嘴唇,直到某天深夜,隔壁刑讯室传来熟悉的咳嗽声——那是她丈夫荀玉坤特有的干咳,还夹杂着日语的说笑声。 这个发现如同惊雷炸响在田仲礁耳边,三个月前,荀玉坤说要去哈尔滨跑药材生意,临走时还把家里仅有的银镯子当了作盘缠。 如今这谄媚的笑声,分明是在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田仲礁突然明白过来:自己被捕前最后一次接头,正是丈夫帮着收拾的针线筐,定是那时被他发现了藏在顶针里的密信。 次日受刑时,田仲礁突然瘫软在地,对着审讯官哀求:"给我纸笔,我全写出来。" 审讯官得意地扔来纸墨,却见她颤抖着手写道:"荀玉坤是双面间谍,他衣襟夹层藏着重要情报。" 这招反间计果然奏效——当夜宪兵队突袭荀玉坤住处,从他贴身衬衣里搜出了田仲礁受刑时偷偷塞进去的假情报,这个叛徒还没来得及辩解,就被当成危险分子秘密处决。 特高课发现上当后,把怒火全倾泻在田仲礁身上,寒冬腊月里,他们把她绑在院中的槐树上,用冰水从头浇到脚;盛夏酷暑时,又把她关进密不透风的铁皮屋。 但无论怎么折磨,这个瘦弱的女人再没吐露半个字,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的坦克碾过东北平原,田仲礁才从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重见光明。 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十指关节全变了形,左耳完全失聪,但眼睛里还闪着光。 此后三年,她跟着四野从松花江打到海南岛,身上的旧伤时常发作,却始终不肯下火线。 这些隐蔽战线的斗士们,就像黑土地上的红高粱,纵使被战火摧折,深埋地下的根系仍在孕育新生。 他们或许没有留下照片,墓碑上甚至没有真名,但那些用鲜血写就的密码,那些在刑具下坚守的信念,早已融进民族记忆的基因里。 当今天的我们翻开泛黄的档案,触摸那些褪色的墨迹时,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灼热的温度。 信息参考: 中央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1991年)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辽宁省志·军事志》(2000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东北抗联地下工作纪实》(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