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位老妇人主动请当汉奸的侄子吃饭。突然,她神秘兮兮地说:“孩子,帮我弄300发子弹!”汉奸一听,放下碗筷说:“您是疯了吗?” 那年秋末的华北平原上,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和硝烟的气息,日军占领区内的某个普通院落里,五十六岁的马宗英正在土灶前忙活。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表面上和村里其他妇女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已经在暗中为八路军传递了三年情报,此刻她正为即将到来的弹药运输任务发愁——部队急需的三百发子弹还卡在县城里运不出来。 这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妇女有着不为人知的经历,年轻时她跟着丈夫参加过农民自卫队,丈夫牺牲后便独自抚养侄子王云蓬长大。 如今侄子成了伪军里的翻译官,这个身份让马宗英既痛心又无奈,但她心里清楚,这个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孩子本性不坏,或许还能争取过来。 腊月初八那天清晨,马宗英特意起了个大早,她把攒了半年的白面揉成面团,将家里最后两只下蛋的母鸡宰了炖汤。 晌午时分,穿着伪军制服的青年推开了斑驳的木门,胸前的铜纽扣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光,王云蓬闻着久违的鸡肉香,脸上的笑容还没完全绽开,就被姑姑接下来的话惊得差点摔了碗。 灶房里的土墙上映出两个人影,一个佝偻着背在灶台前添柴,一个僵直地站在方桌前,马宗英往灶膛里塞了把麦秸,火星子噼啪爆响的声音盖过了侄子急促的呼吸。 王云蓬的后背已经沁出冷汗,制服的硬领子磨得脖子生疼,他当然知道三百发子弹意味着什么,这要是被日本人发现,姑侄俩的脑袋都得挂在城门口示众。 接下来的七天里,马宗英照常纳鞋底、喂鸡鸭,偶尔挎着竹篮去集市买盐,只有半夜躺在炕上时,她才会睁着眼睛听屋外野狗叫唤,盘算着万一事情败露要怎么掩护其他同志转移。 王云蓬那边也不好过,每天在伪军司令部进进出出,看见日本兵腰间的王八盒子就眼皮直跳,他特意挑了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拎着两瓶衡水老白干去找顶头上司喝酒。 伪军后勤处的仓库建在城隍庙旧址上,青砖墙上还残留着香火熏黑的痕迹,王云蓬借着酒劲大倒苦水,说弟兄们巡逻时连实弹训练都不敢搞,生怕浪费子弹挨太君骂。 酒酣耳热之际,他趁势提出要补充些弹药壮胆,上司打着酒嗝大笔一挥,批条子时还笑话他胆子比庙里的泥菩萨还小。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北风卷着雪粒子往人脖领里钻,马宗英推着独轮车出现在城门口,车板上摞着五层竹制蒸笼,新蒸的杂面馍馍冒着热气。 站岗的伪军认得这是翻译官的姑姑,例行公事地掀开蒸笼盖瞅了两眼,最底下那层笼屉里,三百发黄澄澄的子弹藏在发面馍馍中间,裹着油纸包得像年节供品。 根据《华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记载,当时八路军平均每个战士仅有不到20发子弹,马宗英运送的这批弹药,足够武装半个区小队。 这些子弹后来在春季反扫荡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端掉了日军设在马家集的补给站。 运送任务完成后,马宗英依然住在那个不起眼的小院里,她继续给前线的战士们缝制棉袜,把情报藏在纳好的鞋垫里往外送。王 云蓬依旧穿着那身伪军制服,只是从此之后,伪军司令部丢了几箱手榴弹、少了两桶煤油,日本人的清乡计划总像是被戳破的窗户纸。 直到1944年秋天,这个秘密才被揭开,已经升任武工队交通员的马宗英在护送电台时遭遇伏击,弥留之际把藏匿物资的地点告诉了赶来接应的同志。 她坟头的青石碑上没刻名字,只在背面用朱砂画了朵木棉花——当年丈夫参加农民赤卫队时,袖章上就绣着这样的标记。 如今在华北某县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架褪色的竹制蒸笼,旁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码着三百枚复刻的子弹模型。 泛黄的标签上写着简单的说明:"群众自制运输工具,1941年冬",玻璃展柜倒映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那些模糊的面容仿佛与历史中无数个"马宗英"重叠在一起。 (信息来源:《华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冀南军区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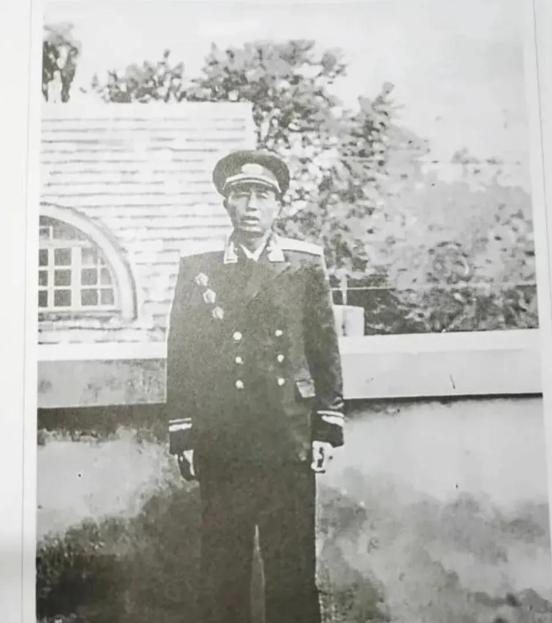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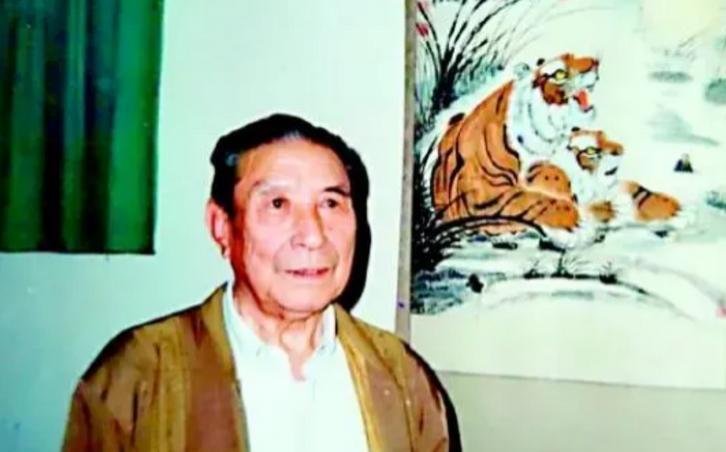


用户17xxx28
叩首[祈祷],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