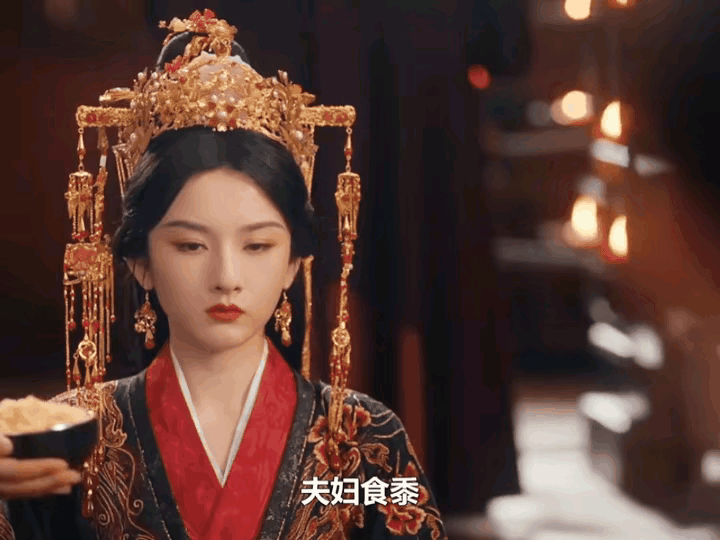98岁北大教授季羡林一针见血:“人老了,躺在病床上才明白,废掉身体最快速的方式,不是抽烟、喝酒、打麻将,而是以下2件事。” 季羡林曾说“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季羡林曾在故乡待了6年,而后背井离乡,曾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过了4年。后也曾在欧洲住了11年,后来又回到北京,到访过世界近30个国家,看过一弯又一弯月亮。 他说“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称自己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他本希望像老师陈寅恪先生一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终身从事于学术研究。然而却阴错阳差,成就了极为复杂的他。 他据此表示“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垂垂老矣,晚年的他,有着更多的感慨,也有着几项习惯,其一便是研究佛教。他曾说,自己在1935年到德国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后,便跟佛教开始结缘了,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年代,尽管研究对象很杂,但是对佛教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兴趣。 有人便问他“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季羡林却对此表示“我从来没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 用认真科学的方法加以探讨,发掘其根源,发现其演变的历史过程,然后再进行深究。马克思曾有过一句类似的话,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所创造的,会有着一定虚幻和麻醉的需要。 季羡林对佛教不全信,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佛心。 除此外,季羡林还是一个坚信和谐说的人。正所谓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季羡林也曾一度坚持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做法,尽量的顺其自然,不大喜,也不大悲,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尽管他是文学大师,也曾在无数场合表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但也曾一度被绯闻纠缠,但他并不在意。 他表示自己尽量做到不亏欠别人,也不让别人亏欠自己,顺其自然,坚持和谐观。后来,在学生问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时,他的答案也是:“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他文章中更是将和谐一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我头顶上滴声未息,而阳台上幽静有加,我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 听雨有着不同的心境,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此时的季羡林,远不是鬓星星了,甚至到了顶上“童山濯濯”的地步,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但他听雨却没有太多悲伤之情,反而更多的是喜悦,他听到头顶上的雨声,总是心旷神怡,那感觉就仿佛身处于麦田里,每一个叶片都张开了小嘴,尽情的吮吸着甜甜的雨滴。 在尝到这天降甘露以后,原本枯黄的叶片都变青了。 季羡林有一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坦然。 时光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之后随着岁月的沉淀,会有不同的心绪,然而也会更加偏向于中庸,会更加偏向于和谐。 季羡林一度想要做到坚持和谐,做到不喜不惧的状态,但随着人至暮年,季羡林未尝没有更多感慨。 比如在看到月季时,他会想护花的主人为何不来浇水呢?是他们已经不再是人间了吗?那谁再照料这些月季呢,未来等待月季的是寂寞,枯萎和死亡。在看到牵牛花时,他感叹牵牛花这种野花没有主人的播种,恐怕连幼牙都长不出来。 越想便越寂寞,被这种寂寞深深的包围和笼罩,甚至一度不想再看到春天,不想看到这些枯萎的月季。 那日,他正好听闻老友在夜间患了疾病,不到几个小时就离开世界,时间是无情的,命运更是无情,人老了很可能一夜睡去,第二日再也醒不来了。 纵而已年届耄耋,已经阅历,太多见证了人情冷暖,万世悲欢。但是在得知此事后,季羡林也无法做到不伤悲,无法做到不震撼,他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虽有伤悲,虽曾遇到困境,虽曾得前列腺癌和膀胱癌,但是他都挨过来了,在提及自己的长寿秘诀时,他写下不妄动、不择食、不萦怀,除此之外,晚年最需要避免的还有两事,这两事比吸烟喝酒更致命。其一便是沉醉于欲望,被欲望驱使,追逐,成为命运的囚徒,等待自己历尽千帆,其实最后最渴望回归的仍然是原点,兜兜转转仍然是圆。 其次,便是心态,主观意志决定精神,对客观事物也有着反作用,始终保持恒定的心态,看淡悲欢,而又积极的看待一切,而不是消极的面对,极为关键。这一点从最后一片枫叶中,便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季羡林说人世间浮云变幻,更多时候要做到尽人事听天命,保持心情的平衡。而时间会见证一切,也会带走一切,会记录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