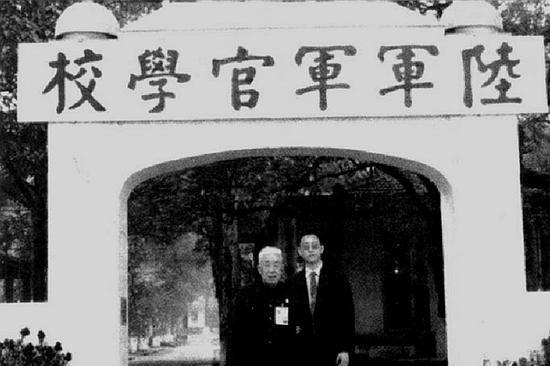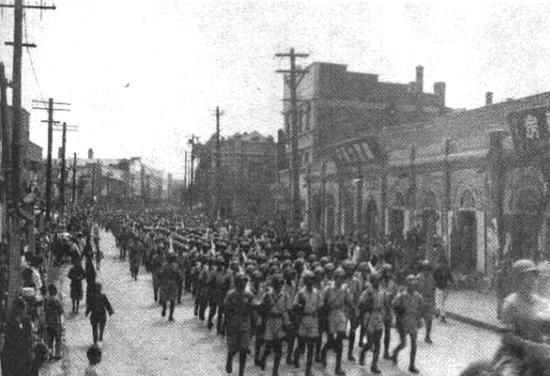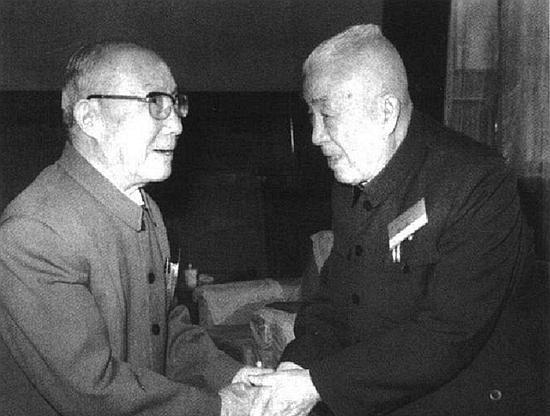50年郑洞国去中南海赴宴,周总理为何叮嘱道: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 “1950年深秋的傍晚,’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周恩来笑着拍了拍郑洞国的肩膀。”这句话给在座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郑洞国彻底放下最后一丝顾虑。短短一句温和却坚定的叮嘱,背后隐藏的是新中国对旧部将领的一整套接收与安置思路,更折射出一名国民党中将由彷徨到投入国家建设的曲折心路。 那顿饭设在中南海丰泽园。丰泽园并不以豪华取胜,大红灯笼、四合院、芭蕉树,营造出的更像是师长家中叙旧的氛围。周恩来特意请来聂荣臻作陪,以“老同学”身份化解郑洞国的拘谨。刚一落座,周恩来给郑洞国倒了杯热茶,随口问:“北京天气干,你还习惯吗?”简单一句问候,却把距离瞬间拉近。 周恩来关心的并非一桩饭局,而是如何让眼前这位昔日劲敌安心留下。郑洞国早在1948年10月长春起义后,就对“归宿”问题充满纠结。战场失利、军法威胁、亲信起义,三重压力把他推到解放军一边,可畏惧、内疚与对蒋介石残留的忠诚,使他一度只想“回乡种地”。在哈尔滨养病期间,他每天翻报纸,心里五味杂陈:国民党连连败退,新政权不断推出土地改革、工商新政,他却像局外人。对于一位戎马二十年的军人而言,那种无所事事比被围困时的饥饿更难熬。 东北局高岗看得明白,先把他留在抚顺,慢慢接触形势;肖劲光、肖华不时登门,既谈养生也谈水利工程,潜移默化地给他“充电”。郑洞国起初警惕,不想再卷入是非,甚至向两位解放军将领再三声明:“我不广播,也不上报。”但当他见到昔日部下逐批安排工作、家人团聚,有了切实的获得感,态度开始松动。时间是最好的说服者。 真正动摇他旧观念的,是1950年春天在上海看到的一条消息:长江流域防汛会议决定修筑荆江分洪工程,主持者是他熟悉的前国民党水利专家傅作义。郑洞国这才意识到,新政府不仅包容,而且懂得用人。如果连傅作义都能转换角色,自己又何必躲在乡下呢? 于是,就有了那年深秋的“中南海一宴”。饭桌上,周恩来并没有开宗明义地谈任命,而是从家事聊到往事。郑洞国提到妻子不愿北上,周恩来放慢语速:“家有变动是难免的,先把身体养好,再想办法。”言至此处,他拿筷子敲敲碟子,像敲响一记鼓点:“不过,你不到五十岁,水利、军政经验都有,国家正缺人才。我怎能让你回家种地?” 这一问,既是态度,更是承诺。郑洞国意识到,退守乡间不是归宿,而是一种逃避。他犹豫片刻,终于答道:“让我再回上海处理些家务,随后报到。”周恩来点头:“身体第一,回来我们好好研究水利规划。” 1951年春节前夕,郑洞国第二次进京。政务院会议室里,周恩来听完他的思想汇报,只说一句:“思想通了就好,岗位随时有。”不久,水利部参事的任命文件送到他手中,级别九级,工资二百七十多元,还配专车。郑洞国自觉待遇偏高,主动降薪到两百四十五元,一直没再调整。在粮价飞涨的困难时期,这份自愿的“缩减”让不少老同志侧目:昔日黄埔一期的“嫡系”竟能做到如此。 随后几年,他跟随水利专家李仪祉、张含英跑遍黄河、淮河、长江,对黄河边堤畔勘测线路,对淮河治理方案提出细节修改建议。1953年安徽蚌埠大坝基槽开挖时,郑洞国跟班值守,亲自丈量泥沙厚度。工人师傅在工棚里开玩笑:“都说这老将军枪法好,现在拿铲比拿枪利索多了。”郑洞国笑呵呵接话:“枪打完了要修兵工厂,铲完了能修大堤,谁轻谁重,一算就明白。”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提出让郑洞国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消息传来,他心里忐忑:自己主要干水利,懂军事但脱离一线已久,是否胜任?毛泽东听汇报后摆摆手:“军事委员会需要各方面经验,你是打过仗、又懂经济建设的人,多一种视角,多一分把握。”这番评价,彰显新中国对旧军人转型的期待,也让郑洞国拾回多年失落的自信。 就在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后不久,他收到一份套红请帖:邀请赴中南海与毛泽东、贺龙、叶剑英共进晚餐。丰泽园里,毛泽东故作诙谐:“郑洞国,好响亮的名字哟!”话音未落,他顺手抽出香烟递给郑洞国,并亲自划火柴点火。郑洞国嘴上说“多谢主席”,心里却翻涌:在黄埔、在南京,从未有人如此对待过一个下级将领,他忽然明白了“人心向背”这个词。 席间,毛泽东问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感受。郑洞国坦言:“读得慢,用得更慢。”毛泽东笑道:“我当年在长沙工人里做宣传,人家不理我,我才体会到立场是怎么回事。要真站到工人那边,脸上、话里,自然就合拍了。”言简意赅的点拨,使郑洞国彻底放下“旁观者”的姿态。之后的几年,他连续三届出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国统区老兵安置、台湾统战、退役军官疗养等事项,他四处奔走,能出面就出面,能跑腿就跑腿。不少人说他“换了头脑”,他却常自嘲:“其实是把脑袋放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