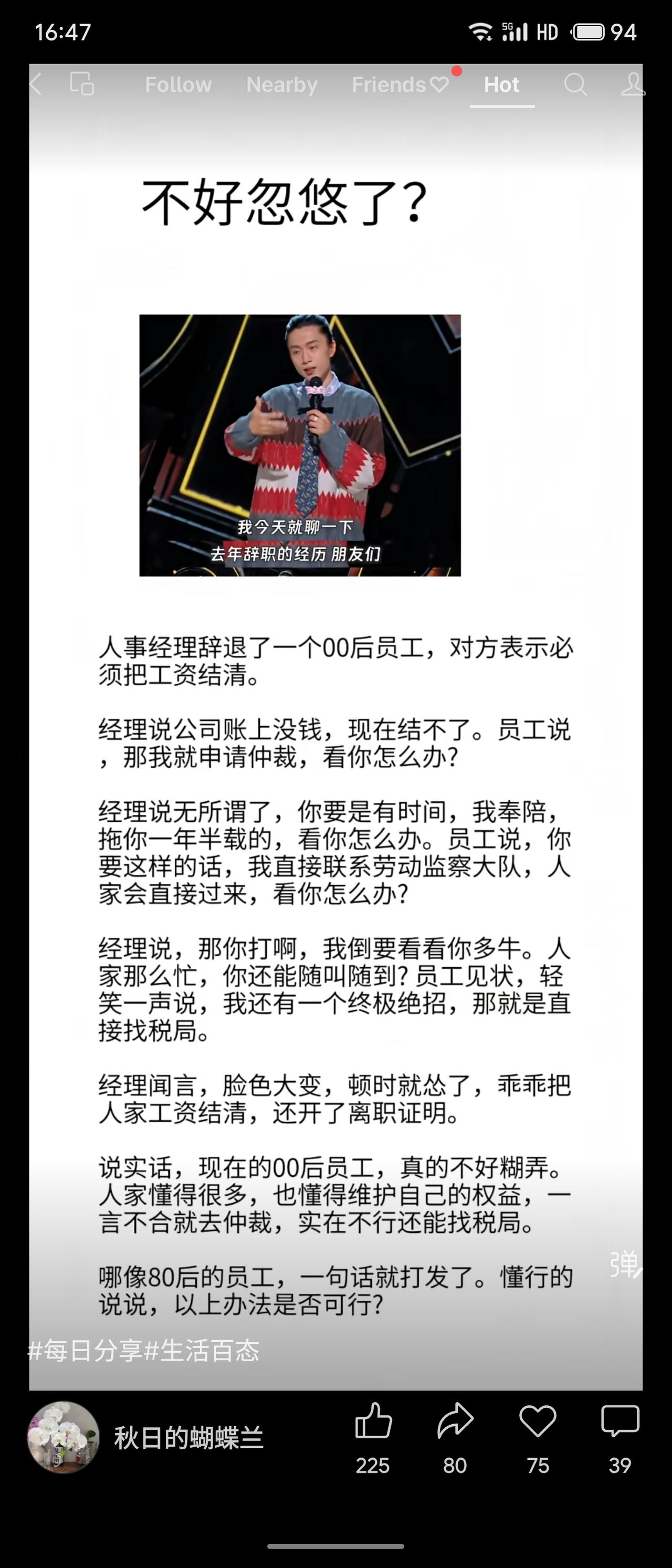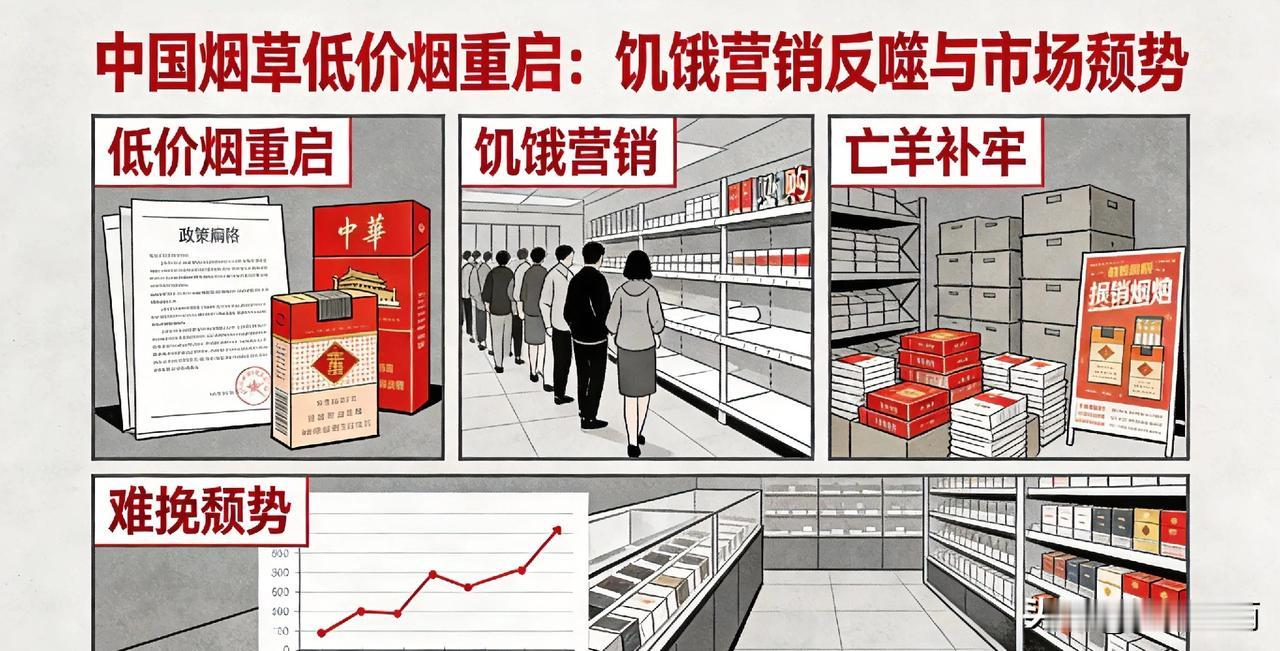时间的分配 劳动时间的长短本身不是一种自由的、个体化的选择,社会范式同样起到作用。一些高调的保守派政治家要求整个社会要“多工作”以促进 GDP 增长。然而大多数的工作岗位是由大型组织机构,而非个体或小微企业创造的。在这些大型组织中,关键的生产资料由企业管理层和远在他方的所有者们控制。管理层决定了劳动的形式,并规定了在这些有着最高生产率组织中工作的方式。 在私营企业中,资本也会以利润的形式要求占用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自凯恩斯 1930年提出预言以来,不仅消费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利润同样也出现了爆炸式的攀升。因此,关于劳动时间的政策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职业道德”或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劳动时间本身,是围绕着人类生命与身体所展开的分配斗争的物质体现。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来,对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在肉体和精神层面上始终是令人感到疲劳的,直到今天这一基本状况依然未曾改变。 无论是在单个企业还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都是如此。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实际上向国外“输出”了劳动时间。以德国为例,2024年的2400亿欧元出口顺差折算下来相当于 34 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约 200 万名全职劳动者一年的工作量。 当然,人们会说市场“必须”被开拓、利润“必须”被实现——这被视为对承担风险的回报,也被认为能为投资创造激励。但这又引出了一个反问:为什么? 如果我们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因为投资者必须获得回报、必须有激励”,那么接下来就要问:谁的奢侈品消费欲望和社会区隔需求应该优先得到满足?我们又在强化怎样的权力结构? 让我们再次回到凯恩斯。我们不应忘记,凯恩斯虽然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倡导“有意义的闲暇生活”的未来愿景之外,他同时提出了“利息食利者阶级的安乐死”这一著名观点,并强烈主张将重要的投资决策社会化。这正是他整个经济理论的核心要义。依赖私人投资者变幻莫测的情绪,只会导致一再重演的危机与衰退。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来促进繁荣,但对凯恩斯而言,真正自由的社会最终必须通过公共对投资的控制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今天依然成立:如果在面向未来的重大决策上,依然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目光狭隘、粗鄙功利的商人身上,那么这个世界最终呈现出的样子也就不足为奇——一个被真人秀、社交媒体网红和无孔不入的广告所主导的世界,一个由缺乏想象力的政客不断呼吁“更努力工作”的世界。 凯恩斯的预言并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科学式的推演。它的目的既不是要机械式地预言未来,更不是要鼓励人们努力工作、拼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相反,他真正的意图是:促使人们以开放且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思考未来。在他的构想中,未来不是一种让人感到恐惧的威胁,而是一种承诺。当他在1930年写下这篇文章时,他所强调的正是一种根本性的乐观态度。 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假设既简单又极具说服力:未来将会截然不同,而且会变得更好。但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那样,这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困扰我们的不再是匮乏,而是我们将如何使用这份新的自由?我们会怎样处理这份“盈余”(Surplus)?这一问题对于今天的我们,与对于1930年的凯恩斯而言,同样紧迫。对于他与我们而言,一场进步式的民主讨论不应从那些以 GDP 增长之名、诉诸“职业道德”的训诫开始,而应从对自身可能性的现实且坚定的评估开始。 附:八小时工作日的收入流向——德国 2024 年国民收入分配 一、资本所得(3 小时 05 分) 折旧成本:1 小时 35 分 利润:1 小时 30 分 二、国家(税 + 社保)(2 小时 28 分) 社会保险(雇主部分):43 分钟 社会保险(雇员部分):34 分钟 工资税:29 分钟 其他税收:42 分钟 三、劳动(净工资)(2 小时 27 分) 住房:47 分钟 其他开支:37 分钟 食品:20 分钟 交通:16 分钟 储蓄:16 分钟 休闲娱乐:12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