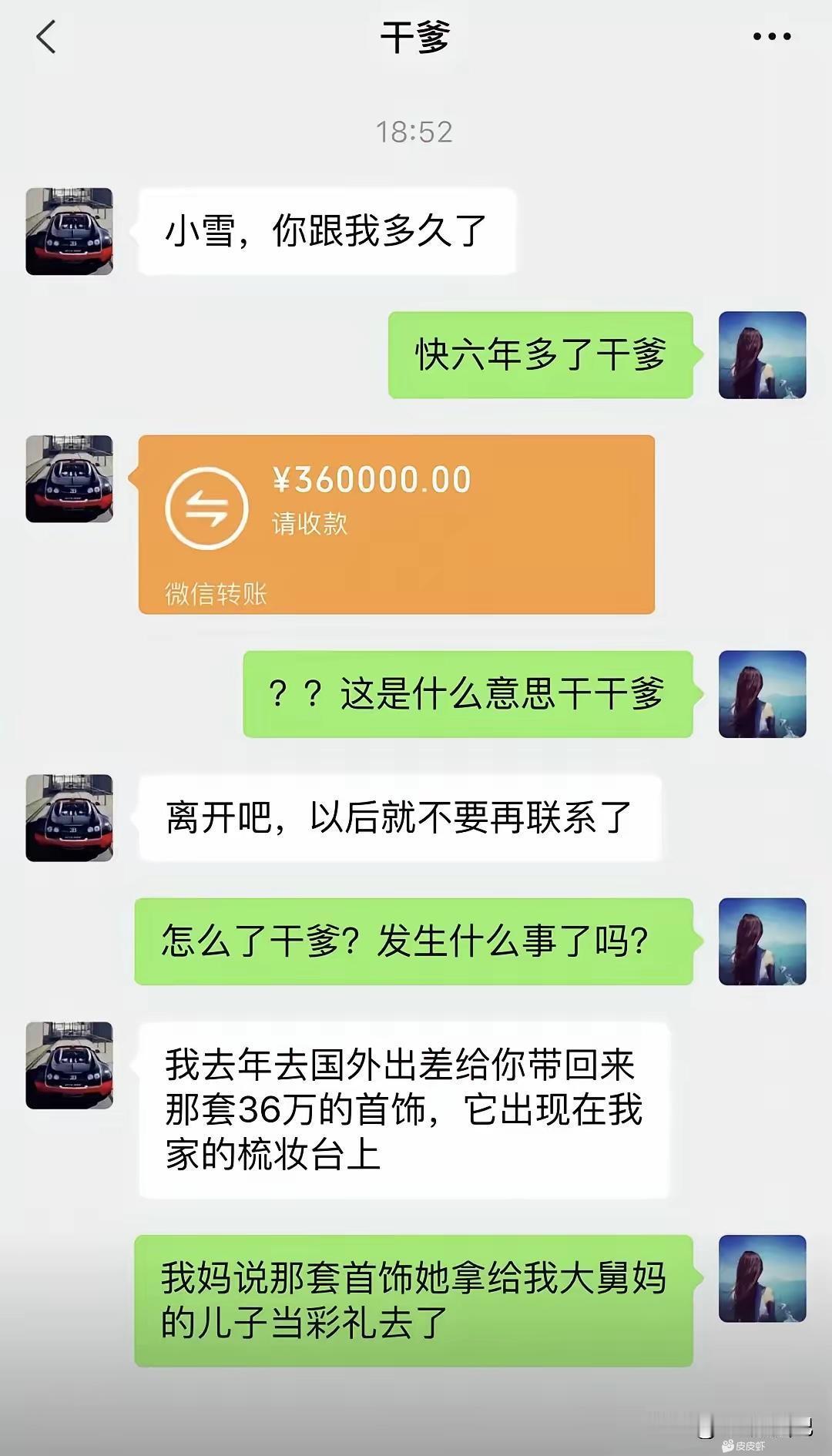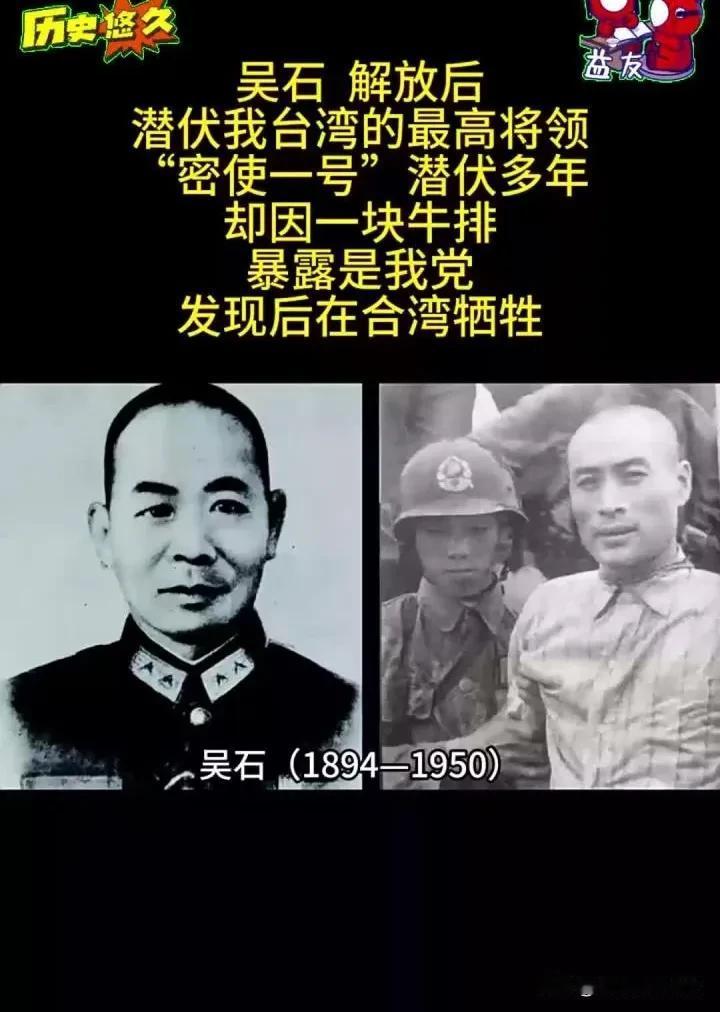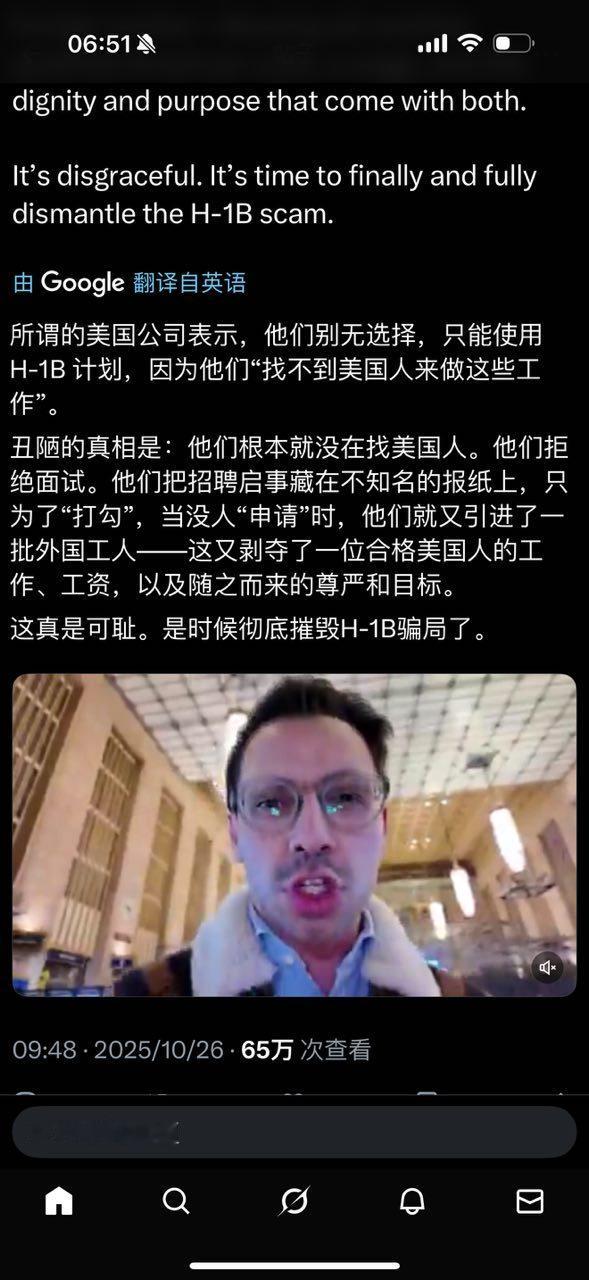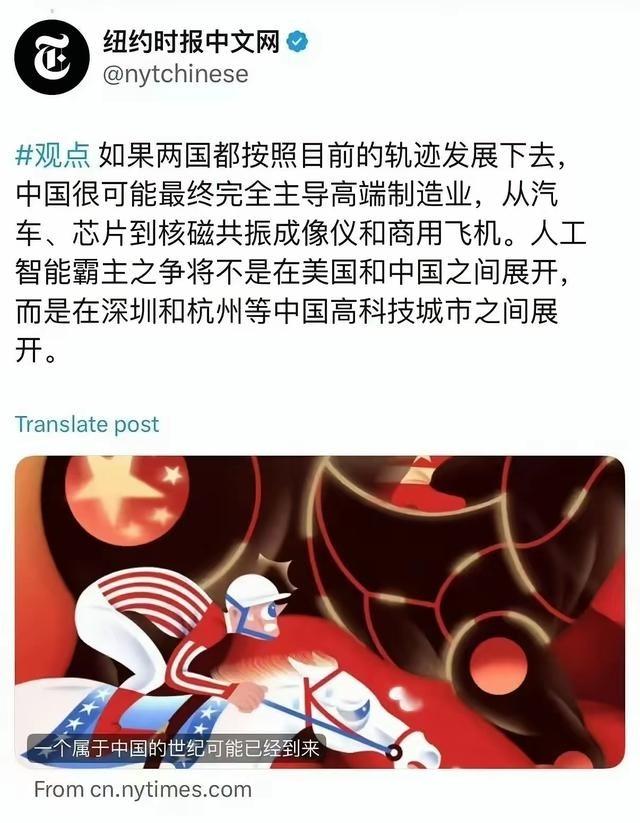开国将校里唯一申请去台湾的人:99岁的母亲病危,想去见最后一面。 黄汉基这个名字,翻课本翻资料也不容易看到,军衔不显眼,1955年授的是上校,空军里有些老人提起他,语气很平,干过两件别人不去碰的事,弃海军走延安,后来又递报告去台湾看母亲,别人退下去养老,他被家和时代两头拉着,不怎么往后退。 他申请去台湾见母亲,99岁,最后一面,这事现在听起来像戏,实际那年真有,他在开国将领里,唯一一个自己起身开口要去的人,档案里有申请书,很多人不知道,也值得拿出来说一遍。 家在福州长乐,海军圈子里的正统人家,爷爷黄钟瑛那辈名头在外,海军总司令,孙中山写过“公而忘私”,葬礼还是孙亲自主持,父亲黄忠璟,北洋政府海军部上校参谋,烟台水师学堂出来,按部就班往上走,技术军官那路子,旧制度里的规矩人,儿子该怎么走,台阶都摆好了。 1936年,他进了马尾海军学校,老校,李鸿章那会儿就开始办,讲英文,教战术,和后来那批打游击的八路,步子不一样,第二年抗战打起来,他瞒着家里退了学,跟几个同学一起“考不及格”出走,徒步往延安去,十八岁,身上背着家族的安排,脚下偏过一条道,他爹不去吵也不去闹,往延安寄邮票,那个年代邮票能换东西,一张能换一碗红烧肉,他爸一共寄了一百多张,他在一一五师情报科,翻译日军战报,拿邮票换的那点咸肉慢慢啃,夜里灯小,心里惦记家,父子没互相说服,线没断,这就是黄家人相处的法子。 延安分配随缘,他英语顶用,进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当参谋,在情报口里干,从山东一路到东北,再往湖南,他不在最前面指挥冲锋那种位置,坐在桌边编译敌情报告,写作战方案,做联络翻译,很多前线干部英文看不懂,日本军方和美方情报有英文往来,这时候他这种人就顶住了,他跟罗荣桓,陈光一起干,在山东当过军区情报处科长,后面去东北,东北民主联军一纵作战科长,334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四平,锦州,沈阳,跟着打,再南下长沙,番号换来换去,他跟紧,台阶也上得快,出身海军家庭,成了陆军干部,建国之后又转到空军,三条兵种都踩过。 1949年后整编,海军要建军,萧劲光听人说他是马尾出身,想着调他回海军当骨干,空军那边刘亚楼知道这人,东北一起打过,觉得他稳,话少,脑子清,适合做军事教育和指挥,刘亚楼一句话把人要过去,空军收了,黄汉基不多讲,直接去了,第三段军旅开始,空军教育系统的老前辈,办了三个航校,中国第一个轰炸团也从他手里拉起来,带出来一批又一批学员,抗美援朝,他在空军十师,参与指挥攻占大和岛,回来以后,一航校校长,十六航校校长,最后去空军气象学校,三所学校里都有人后来当了将军,周总理签的任命书,家里一直放着,等到他去世还在柜子里。 从1936年离家,他没再见过父母,他以为家人留在福建,实际父亲在1949年撤退时带着家去台湾,两边的世界隔开了,联系不大容易,母亲魏韶琴读过师范,脑子清清楚楚,记儿子的生日,心里一直有个问号,人还在不在,在哪边,她常念叨一句,我的依基还在吗。 依基是他的小名,这句,妹妹黄汉琳记了三十年,八十年代初她在美国教书,有点资源,开始找哥哥,给解放军总政写信,信在系统里转了好几道,最后落到了他桌上,那时他六十多,接电话,手里捏着听筒愣了一阵,妹妹寄来母亲录的磁带,担心福州话他听不全,配了翻译稿,他把磁带放枕边,一晚上来来回回听了八次,那年他没动身去台湾。 真正让他提申请的,是1990年母亲突然病危,99岁,床边人不多,她就想见一面儿子,他递报告,写明赴台探亲,这一张纸不是普通的探亲条,开国将校去到那个岛,归在特例,按当时的规矩算敏感,他的审批最后过了,理由直来直去,母亲百岁将终,亲情不等人。 1990年冬,他穿着空军大衣,从北京起飞,过香港,转台北,到了门口,脚步慢了一下,屋里灯光不强,他走到病床边,凑近耳边,说,妈,汉基回来了,老太太前几天不清醒,这一刻睁眼,眼眶湿,脸上有两道水痕,他没多说话,她看着他,眼睛不走神,后面慢慢恢复了一些,两个多月在他陪着下走完,终年101岁。 他后来不去讲这段路,2003年他走了,子女收拾遗物,抽屉里翻出那张赴台申请书,还有那盘磁带,他一辈子没留豪言,留了一条路,他军衔不高,不是宣传里的英雄形象,办学校,做训练,战功也不往外摆,他那趟去台湾看母亲,是别人没去做的,他拿自己的名头和身份,替这边和那边之间,先走了一条亲情的道,没鼓噪,也没人敲锣,他先迈出去一步,后面慢慢有了回乡老兵。 有了赴陆探亲,有了两岸婚姻,他走时83岁,墓碑不大,空军统一样式,铭文里没写他的家世,也没写他看过母亲最后一眼,空军圈的老人提起他,口里会带上一句,黄校长是第一个申请去台湾的人,以后有人会记住这个名字,记的不是他打过几场仗,记的是他背着枪穿着军装,站在母亲床边,开口说,妈,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