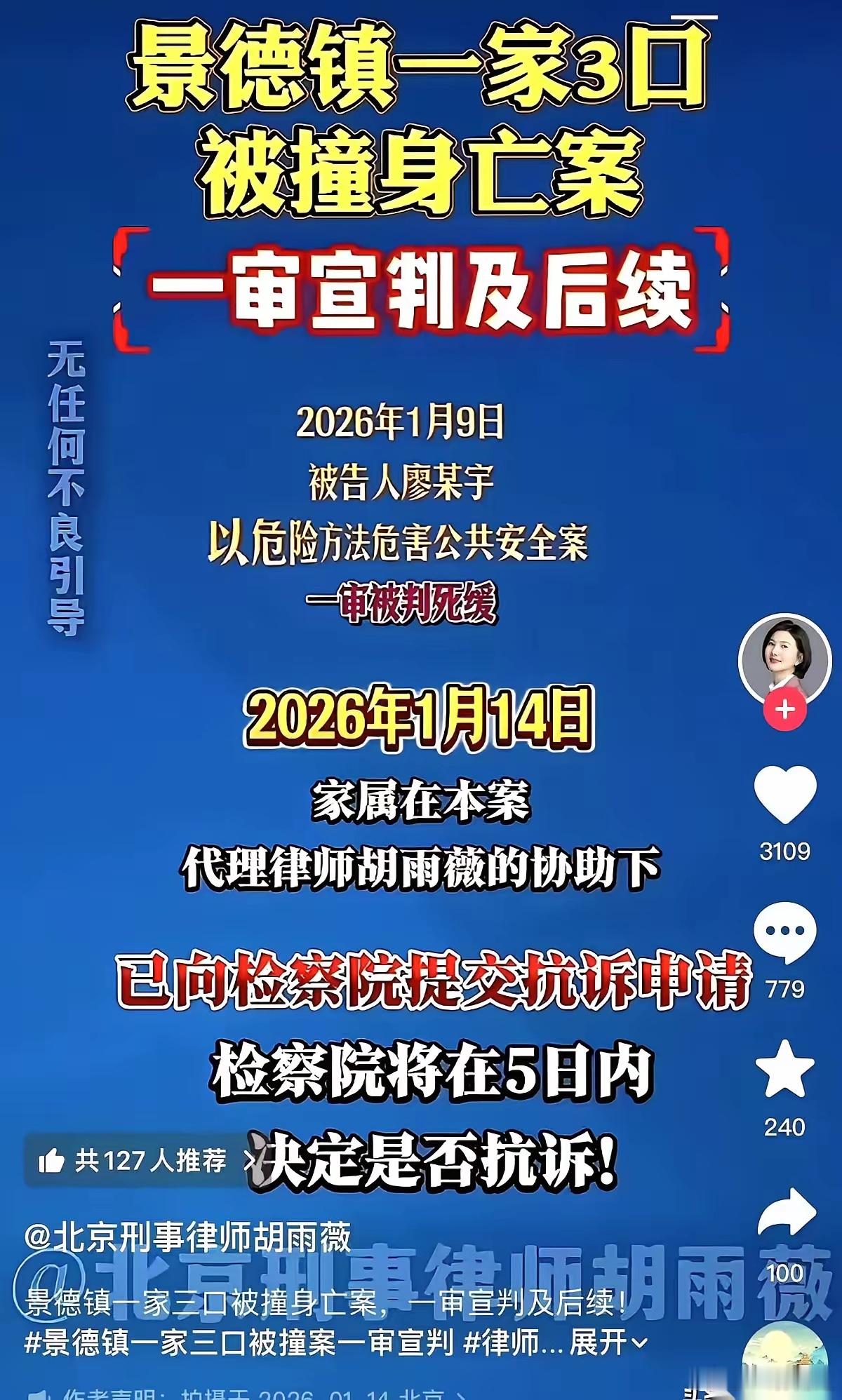北京一流浪汉因无暂住证被送进收容所,填写籍贯时警察瞬间呆住“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搁90年代末的北京,没暂住证被收容可不是新鲜事。1991年国务院就明确收容对象包括“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的流动人员,1992年后这制度彻底脱离了最初救助灾民的福利性质,变成了管理流动人口的强制手段。那会儿农民工进城可不容易,1994年劳动部出台规定,跨省务工得先在老家办“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到了城里再换“外来人员就业证”,证卡合一才能合法干活,少一样都可能被当成“盲流”收容 。王耀军遇到的,正是那个年代无数外来者都躲不开的“证件门槛”。 警察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杞县王耀军”这名字,在豫东蒜乡曾是响当当的招牌。杞县从1981年就开始试点种植大蒜,王耀军是80年代末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会儿农村刚包产到户,村民还守着亩产千斤的粮食田发愁,他已经跑遍山东、江苏,引进了高产的“白玉蒜”,还跟着县农技站学了地膜种植技术。“那会儿蒜亩产直接从2000斤冲到3500斤,收购价也从两毛五一斤涨到七毛,种一亩蒜顶三亩小麦!”这是当时杞县村民的共识。他牵头成立的合作社,是全县第一家正经的大蒜产销组织,带动周边五个村种了上千亩蒜,县里给他评“致富能手”时,报纸上还登了他抱着大蒜的照片。 变故发生在1995年前后。那年全国大蒜产能过剩,杞县大蒜收购价从之前的七毛一斤,一下子跌到一毛多,有的收购点甚至压到八分一斤。屋漏偏逢连夜雨,连续两年倒春寒冻坏了蒜苗,亩产直接砍半。王耀军之前跟村民拍着胸脯保价,说“就算市价跌,我也按五毛一斤收”,为了兑现承诺,他不仅投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两万多块高利贷。更糟的是,他爱人突发脑梗,住院押金就要八千,那时候农村还没医保,这笔钱在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放下脸面,揣着仅剩的身份证和合作社的公章,偷偷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他本想凭着种蒜的手艺,在城郊找个蔬菜基地干活,没成想刚到北京站,口袋就被小偷划了,身份证、公章全没了。没有身份证,就办不了外出就业登记卡,更别提暂住证和务工证,正规工地根本不敢收留他——那会儿老板招无证工人,查到了要罚巨款。他只能在桥洞落脚,靠拾荒度日,饿了就啃干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慢慢成了别人眼里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认出他的警察叫李建国,老家就在杞县邻乡,1990年跟着父亲去买蒜种,亲眼见过王耀军在乡礼堂讲课。“您当年教大家‘蒜茎留1.5厘米晾晒,不能暴晒’,我家现在还这么存蒜呢!”李建国的话,让一直沉默的王耀军红了眼眶。他攥着收容所的登记表,指节都捏白了,半天憋出一句:“没想到,还能有人认出我。” 王耀军的遭遇,不是个例。那个年代,收容遣送制度的“自愿”与“强制”界限模糊,很多像他这样有手艺、有担当的人,就因为证件不全被贴上“盲流”标签。更让人无奈的是,当时进城务工还要交各种杂费,暂住费、管理费一项都不能少,就算证件齐全,这些开支也让农民工压力山大,直到2002年国家才取消这些收费。王耀军有头脑、肯吃苦,却因为丢了身份证,被制度门槛挡得寸步难行,从致富带头人变成流浪汉,这背后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在时代浪潮中的无力。 2003年孙志刚事件曝光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自愿救助制度,暂住证后来也逐渐被居住证取代,外来人口终于不用再为“无证”惶惶不可终日 。2001年杞县成立了蒜业集团公司,统一负责大蒜的种植、储存和销售,再也不会出现“菜贱伤农”的情况,现在杞县大蒜已经远销50多个国家,成了真正的“金字招牌” 。但王耀军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时代城乡流动的壁垒。 他不是好吃懒做的流浪汉,也不是无家可归的游民,只是在时代浪潮中摔了跟头,又被制度门槛挡了去路。如果当年证件管理能灵活一点,如果收容制度多些人性化考量,如果农村医保能早几年普及,他或许不会落到那般境地。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流浪汉,背后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落魄,未必是个人懒惰,可能是意外变故,可能是时代局限,也可能是制度漏洞。而一个文明的社会,不该只靠证件定义一个人的价值,更该给困境中的人多一点包容和机会。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