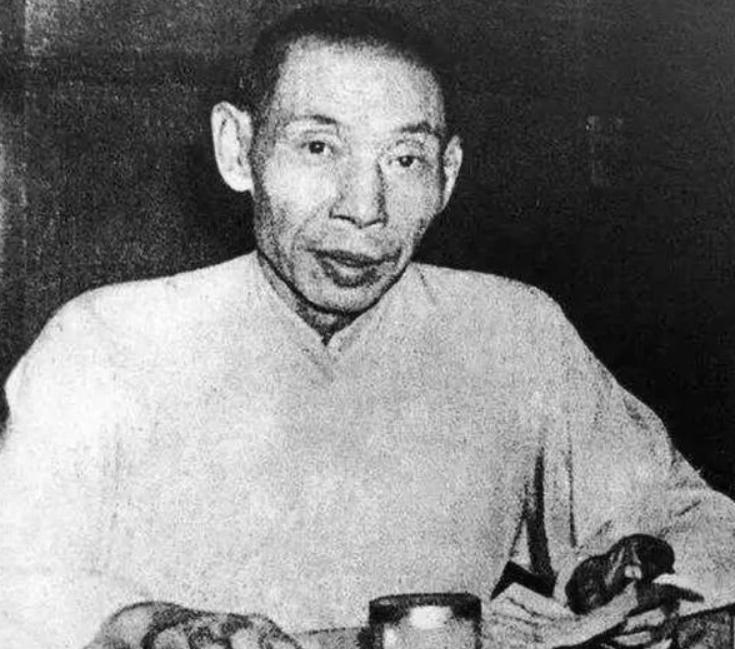1945年9月,杜月笙前往上海,认为当不了市长至少也是副市长。火车快到上海时,蒋介石委任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为上海市长,杜月笙的门徒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 1937年,淞沪会战打得天昏地暗。老蒋,也就是蒋介石,心里急啊。上海这地方,龙蛇混杂,光靠正规军,很多事情不好办。他得找个地头蛇,一个能镇得住场子、一呼百应的人。找谁?蒋介石的算盘打到了杜月笙头上。 这事儿派谁去说最合适?戴笠。戴笠跟杜月笙那是什么交情?说起来有点意思。当年戴笠还是个小混混的时候,就在杜月笙的赌场里玩骰子,技术高超,把赌场给镇住了。杜月笙一看,嘿,这小子不简单,是个人物。当场就结拜了。你说这叫啥?这就是杜月笙一辈子信奉的哲学:钱财用的完,交情吃不光。他存的不是钱,是人情。 所以戴笠一开口,杜月笙二话没说,就应下了。要人出人,要力出力。他愣是动员青帮、工人、学生,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特别行动队”,番号叫“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这支队伍,在上海的街头巷尾,跟日本人玩命。他们搞突袭、玩狙杀、探情报,救助难民。虽然最后仗打输了,这支队伍伤亡惨重,两千七百多个弟兄没了,但杜月笙的这份力,老蒋是看在眼里的。 蒋介石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元首,怎么会跟一个青帮头子合作?嗨,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复杂性了。老蒋的策略,说白了就是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在上海那个地界,杜月笙的能量比政府公文好使。他一句话,码头工人能停工,工厂能关门。这种力量,在战争时期,是必须团结和利用的。 除了出人,杜月笙还出钱。当时的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急需通讯器材,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杜月笙知道了,直接下令把自己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给拆了,送到前线去。上海沦陷后,他更是花大价钱买《西行漫记》这些进步书籍,送到租界里的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 日本人那边呢,也盯着他。想拉拢他,跟他合作开银行,一起赚中国人的钱。杜月笙怎么回的?他托人带话:“我杜月笙就算穷死、饿死,也绝不当汉奸。”这话,他说得斩钉截铁。 更绝的还在后头。1939年,汪精卫跟日本人签了卖国密约。汪的随行高宗武、陶希圣两个人,良心发现,揣着密约的副本就跑了。这要是让汪精卫的人抓回去,小命不保,密约也得石沉大海。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消息,立马飞到重庆报告老蒋,同时安排自己在上海的头号门徒万墨林,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两人从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救出来。这场营救,跟电影演的似的,惊心动魄,最后硬是把人给安全送走了。 干了这么多事,桩桩件件都是提着脑袋在干,都是在为老蒋的国民政府卖命。杜月笙心里能没点想法吗?他觉得自己这份“投资”,怎么也该到“分红”的时候了。 可事情就坏在,他不仅仅是个“爱国者”,他还是个“生意人”。1943年,他在重庆搞了个“通济公司”。这公司是经过蒋介石默许的,用后方的战略物资,去换沦陷区的棉纱。这事儿在当时,确实缓解了后方的物资短缺。但问题是,你这是在跟敌人做生意啊。不管初衷如何,落在别人眼里,就成了“大发国难财”。这一下,杜月笙的形象就复杂了,也给了政敌们攻击他的口实。 所以,当1945年,杜月笙的火车轰隆隆地快要开进上海站的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一封电报传来,老蒋的任命下来了: 上海市长,钱大钧。 副市长,吴绍澍。 警察局长,宣铁吾。 钱大钧,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心腹中的心腹。吴绍澍,他是杜月笙的门徒。让徒弟当副手,看着自己的老板,这手腕,够可以的。既安抚了杜月笙的势力,又埋下了一颗钉子。宣铁吾,军统的干将,警察局这种要害部门,必须交给最信得过的人。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杜月笙当场就懵了。他心里明镜儿似的,这不是简单的职位安排,这是蒋介石在告诉他:杜先生,你的时代过去了。 抗战的时候,你需要地头蛇的力量,需要有人帮你处理那些政府处理不了的脏活累活。现在抗战胜利了,要建国了,要讲法统了。上海作为中国的门面,市长怎么能是一个青帮出身的人物?在国内怎么服众? 说到底,杜月笙一生精于“会做人”,他看透了无数人心,却终究没能完全看透和蒋介石的关系。他以为他跟老蒋是合伙人,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可在老蒋眼里,他们的关系更像是一种临时的、基于利益的联盟。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八个字,杜月笙在那个瞬间,应该是体会得淋漓尽致。他为上海流过血,出过力,甚至可以说,没有他,上海的抗战局面会更难看。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因为任何人的功劳而停留。 他回到上海,终究只是一个“社会贤达”,一个被供起来的符号。他昔日的权势和影响力,在国家机器面前,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后来他远走香港,在病榻上销毁了所有的借条,对子女说“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也算是一种彻悟吧。一代枭雄,最终客死异乡,连魂归故里的愿望都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