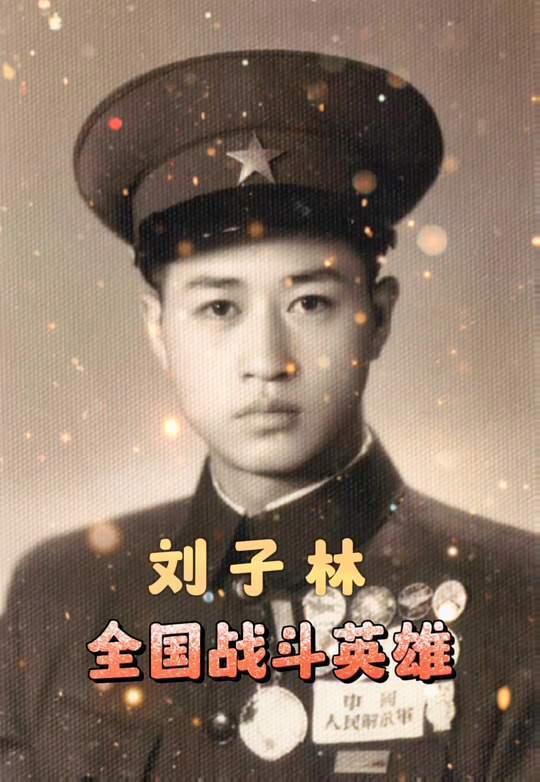1935年11月13日,一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近距离连开3枪。第一颗子弹从后脑射入,前额穿出,脑浆四溅,孙传芳当即倒地;第二颗子弹从太阳穴打入,前额穿出;第三颗子弹从腰部射入,前胸穿出,3枪后孙传芳当即死亡。 1925年,那会儿的中国,就是个大号的“斗兽场”,各路军阀抢地盘、争码头,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人命跟草一样。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是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的军长。当时,直系军阀孙传芳势头正盛,跟奉系在安徽蚌埠一带干上了。施从滨是前线总指挥,可惜,他碰上的是孙传芳。 孙传芳这人,外号“笑面虎”,打仗是把好手,但为人极其阴狠。施从滨兵败被俘,按当时军阀之间的“潜规则”,一般不杀俘虏,特别是高级将领,留着还有用。可孙传芳偏不,他不仅要杀,还要往死里羞辱。 他下令把施从滨斩首,然后把头颅挂在蚌埠火车站门口,悬首示众三天三夜。旁边还挂着一条白布,上面写着七个大字:“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这是诛心,是把一个人的尊严踩在脚下,再碾成粉末。 这消息传回施家,天就塌了。施剑翘那年才20岁,一个养在深闺的女子,一夜之间,心里就只剩下一件事:报仇。她在诗里写:“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改变了。 一个弱女子,要去杀一个手握重兵的大军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施剑翘一开始,也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她先是求自己的堂兄施中诚。施中诚当时在她父亲手下,血气方刚,也发誓要给大伯报仇。施剑翘动用家里的关系,一路扶持他,官至烟台警备司令。可几年过去,官做大了,权在手了,当年的誓言也随风散了。他反过来劝施剑翘:“都过去这么久了,算了吧,别再折腾了。” 施剑翘听完,心凉了半截。她什么也没说,只写了一封信,跟这位堂兄断绝了关系。 堂兄靠不住,她又把希望寄托在丈夫施靖公身上。施靖公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旅长,婚前信誓旦旦,说一定帮她报仇。可婚后呢?一拖再拖,总说“时机不成熟”。到了最后,他甚至开始埋怨施剑翘:“你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搞这些事,真是不守妇道!” 这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带着两个儿子,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丈夫家。 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要想报仇,只能靠自己。 1935年,孙传芳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威风八面的“五省联帅”了。他兵败下野,隐居在天津英租界,过起了念经拜佛的“退休生活”,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的理事长。 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放下屠刀,念起了阿弥陀佛。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讽刺。 施剑翘带着儿子也搬到了天津。她的人生,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她打听到孙传芳的女儿在某小学上学,就把自己的儿子也送了进去。每天借着接送孩子的机会,暗中观察孙传芳的样貌、身形和出行规律。 为了能近距离接触,她甚至化名“董慧”,加入了孙传芳主持的居士林,成了和他一起诵经的“居士”。她摸清了孙传芳的习惯:每周三和周六,雷打不动,都会来居士林参加法会。 1935年11月13日,这一天终于来了。天气阴冷,居士林里香烟缭绕。施剑翘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人群里。她借口后排太热,悄悄换到了一个离孙传芳更近的位置——就在他的斜后方。 下午三点多,住持开始领诵《金刚经》。当所有人闭目合掌,虔诚诵经的那一刻,整个佛堂里最清醒的人,就是施剑翘。她冷静地从宽大的衣袖里,掏出那把早已准备好的勃朗宁手枪。 “砰!”第一颗子弹从后脑射入,前额穿出。 “砰!”第二颗子弹击中太阳穴。 “砰!”第三颗子弹射入腰部。 枪枪致命,毫不拖泥带水。上一秒还在念经超度亡魂的孙传芳,下一秒就脑浆四溅,倒在了自己的蒲团上,当场毙命。 佛堂大乱。施剑翘没有逃跑,她平静地对惊慌失措的人群说:“大家别怕,我叫施剑翘,是为父报仇,不会伤害任何人。” 她将早已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传单撒向空中,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动机。然后,她让在场的人报警,自己则静静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这件事,瞬间引爆了全国舆论。报纸、电台,铺天盖地都是对“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的报道。一场关于“法理”与“人情”的大辩论就此展开。 最后,一审,施剑翘被判十年。二审,改判七年。但民间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下达特赦令,施剑翘被当庭释放。 走出监狱的施剑翘,成了一个传奇。但她自己,却刻意地回避着这份“荣耀”。她很少再提那件轰轰烈烈的事。 抗战爆发,她四处奔走,为前线将士募捐,曾带头捐献飞机。新中国成立后,她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自己则在1957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的她,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在五台山和碧云寺静养。 1979年,施剑翘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她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